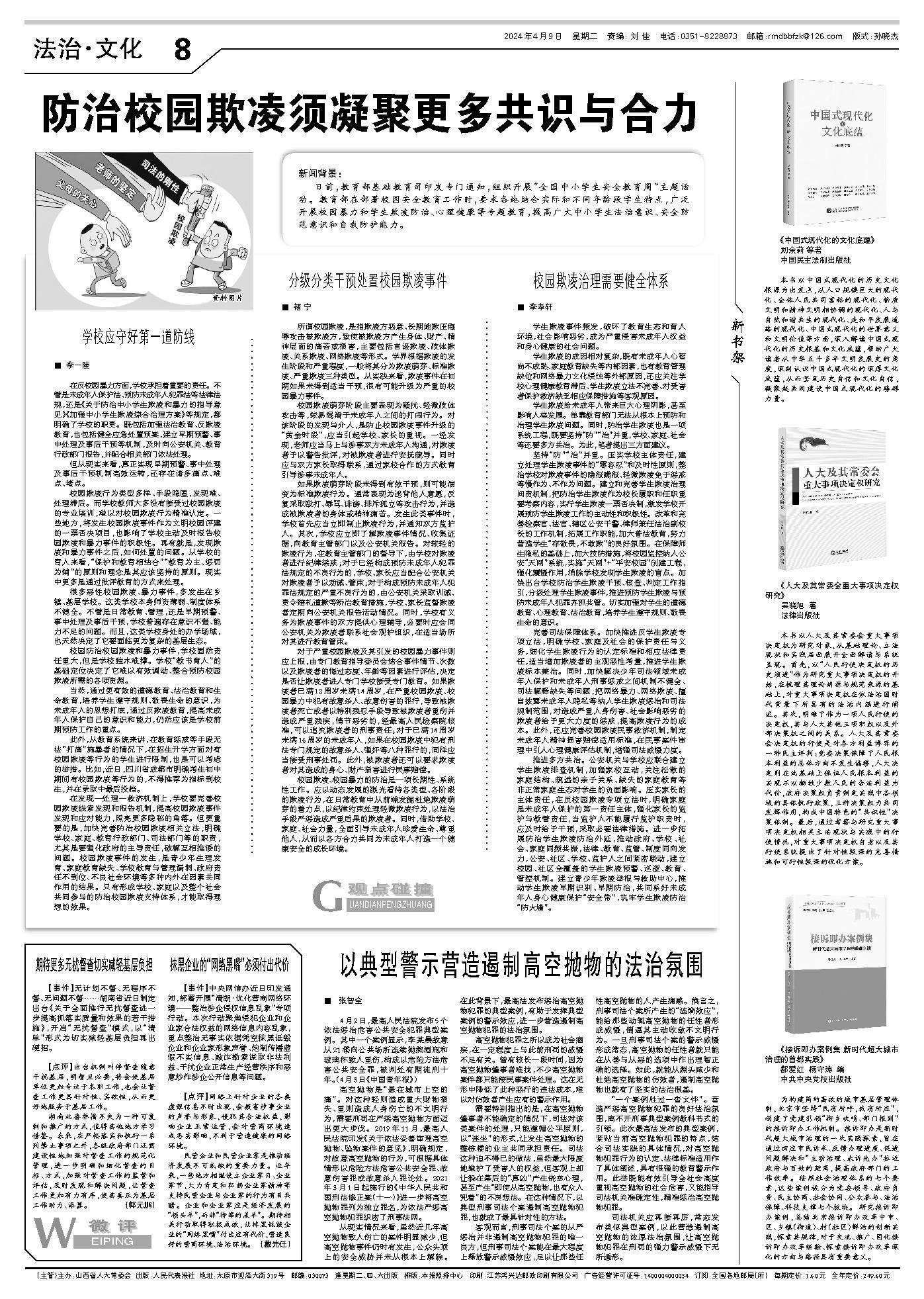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印发专门通知,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主题活动。教育部在部署校园安全教育工作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和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广泛开展校园暴力和学生欺凌防治、心理健康等专题教育,提高广大中小学生法治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学校应守好第一道防线
■ 李一陵
在反校园暴力方面,学校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不管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还是《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等规定,都明确了学校的职责。既包括加强法治教育、反欺凌教育,也包括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建立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等机制,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但从现实来看,真正实现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机制高效运转,还存在诸多痛点、难点、堵点。
校园欺凌行为类型多样、手段隐匿,发现难、处理滞后。而学校教师大多没有接受过校园欺凌的专业培训,难以对校园欺凌行为精准认定。一些地方,将发生校园欺凌事件作为文明校园评建的一票否决项目,也影响了学校主动及时报告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积极性。再有就是,发现欺凌和暴力事件之后,如何处置的问题。从学校的育人来看,“保护和教育相结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理念是其应该坚持的原则。现实中更多是通过批评教育的方式来处理。
很多恶性校园欺凌、暴力事件,多发生在乡镇、基层学校。这类学校本身师资薄弱、制度体系不健全。不管是日常教育、管理,还是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学校普遍存在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这类学校身处的办学场域,也天然决定了它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基层生态。
校园防治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学校固然责任重大,但是学校独木难撑。学校“教书育人”的基础定位决定了它难以有效调动、整合预防校园欺凌所需的各项资源。
当然,通过更有效的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和生命教育,培养学生遵守规则、敬畏生命的意识,为未成年人的思想打底,通过反欺凌教育,提高未成年人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仍然应该是学校前期预防工作的重点。
此外,从教育系统来讲,在教育惩戒等手段无法“打痛”施暴者的情况下,在招生升学方面对有校园欺凌等行为的学生进行限制,也是可以考虑的举措。比如,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明确考生初中期间有校园欺凌等行为的,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并在录取中最后投档。
在发现—处理—救济机制上,学校要完善校园欺凌线索发现和报告机制,提高校园欺凌事件发现和应对能力,照亮更多隐秘的角落。但更重要的是,加快完善防治校园欺凌相关立法,明确学校、家庭、教育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等的职责,尤其是要强化政府的主导责任,破解互相推诿的问题。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是青少年生理发育、家庭教育缺失、学校教育与管理漏洞、政府责任不到位、不良社会环境等多种内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形成学校、家庭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校园欺凌支持体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分级分类干预处置校园欺凌事件
■ 褚 宁
所谓校园欺凌,是指欺凌方恶意、长期地欺压侮辱攻击被欺凌方,致使被欺凌方产生身体、财产、精神层面的痛苦或损害,主要包括言语欺凌、肢体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形式。学界根据欺凌的发生阶段和严重程度,一般将其分为欺凌萌芽、标准欺凌、严重欺凌三种类型。从实践来看,欺凌事件在初期如果未得到适当干预,很有可能升级为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
校园欺凌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骚扰、轻微肢体攻击等,较易混淆于未成年人之间的打闹行为。对该阶段的发现与介入,是防止校园欺凌事件升级的“黄金时段”,应当引起学校、家长的重视。一经发现,老师应当马上与涉事双方未成年人沟通,对欺凌者予以警告批评,对被欺凌者进行安抚疏导。同时应与双方家长取得联系,通过家校合作的方式教育引导涉事未成年人。
如果欺凌萌芽阶段未得到有效干预,则可能演变为标准欺凌行为。通常表现为违背他人意愿,反复采取殴打、辱骂、诽谤、排斥孤立等攻击行为,并造成被欺凌者的身体或精神痛苦。发生此类事件时,学校首先应当立即制止欺凌行为,并通知双方监护人。其次,学校应立即了解欺凌事件情况、收集证据,向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报告。对较轻的欺凌行为,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督导下,由学校对欺凌者进行纪律惩戒;对于已经构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不良行为的,学校、家长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对欺凌者予以劝诫、管束;对于构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采取训诫、责令赔礼道歉等矫治教育措施,学校、家长监督欺凌者定期向公安机关报告活动情况。同时,学校有义务为欺凌事件的双方提供心理辅导,必要时应会同公安机关为欺凌者联系社会观护组织,在适当场所对其进行教育管束。
对于严重校园欺凌及其引发的校园暴力事件则应上报,由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结合事件情节、次数以及欺凌者的悔过态度、年龄等因素进行评估,决定是否让欺凌者进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如果欺凌者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在严重校园欺凌、校园暴力中犯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罪行,导致被欺凌者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导致被欺凌者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追究欺凌者的刑事责任;对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在校园欺凌中犯有刑法专门规定的故意杀人、强奸等八种罪行的,同样应当接受刑事处罚。此外,被欺凌者还可以要求欺凌者对其造成的身心、财产损害进行民事赔偿。
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的防治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应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各类型、各阶段的欺凌行为,在日常教育中从前端发掘杜绝欺凌萌芽的着力点,以纪律约束处理轻微欺凌行为,以法治手段严惩造成严重后果的欺凌者。同时,借助学校、家庭、社会力量,全面引导未成年人珍爱生命、尊重他人,从而以各方合力共同为未成年人打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
校园欺凌治理需要健全体系
■ 李孝轩
学生欺凌事件频发,破坏了教育生态和育人环境,社会影响恶劣,成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和身心健康的社会问题。
学生欺凌的成因相对复杂,既有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家庭教育缺失等内部因素,也有教育管理缺位和网络暴力文化侵蚀等外部原因,还应关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滞后、学生欺凌立法不完善、对受害者保护救济缺乏相应保障措施等客观原因。
学生欺凌给未成年人带来巨大心理阴影,甚至影响人格发展。单靠教育部门无法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学生欺凌问题。同时,防治学生欺凌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坚持“防”“治”并重,学校、家庭、社会等还要多方共治。为此,笔者提出三方面建议。
坚持“防”“治”并重。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建立处理学生欺凌事件的“零容忍”和及时性原则,整治学校对欺凌事件的隐报瞒报、轻微欺凌免于惩戒等慢作为、不作为问题。建立和完善学生欺凌治理问责机制,把防治学生欺凌作为校长履职和任职重要考察内容,实行学生欺凌一票否决制,激发学校开展预防学生欺凌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改革和完善检察官、法官、辖区公安干警、律师兼任法治副校长的工作机制,拓展工作职能,加大普法教育,努力营造学生“存敬畏,不敢欺”的良好氛围。在保障师生隐私的基础上,加大技防措施,将校园监控纳入公安“天网”系统,实施“天网”+“平安校园”创建工程,强化震慑作用,消除学校发现学生欺凌的盲点。加快出台学校防治学生欺凌干预、核查、判定工作指引,分级处理学生欺凌事件,推进预防学生欺凌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齐抓共管。切实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心理教育、法治教育,培养学生遵守规则、敬畏生命的意识。
完善司法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反学生欺凌专项立法,明确学校、家庭及社会的保护责任与义务,细化学生欺凌行为的认定标准和相应法律责任,适当增加欺凌者的主观恶性考量,推进学生欺凌标本兼治。同时,加快解决少年司法领域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刑事惩戒之间机制不健全、司法解释缺失等问题,把网络暴力、网络欺凌、擅自披露未成年人隐私等纳入学生欺凌惩治和司法规制范围,对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社会影响恶劣的欺凌者给予更大力度的惩戒,提高欺凌行为的成本。此外,还应完善校园欺凌民事救济机制,制定未成年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标准,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引入心理健康评估机制,增强司法威慑力度。
推进多方共治。公安机关与学校应联合建立学生欺凌排查机制,加强家校互动,关注松散的家庭结构、疏远的亲子关系、缺失的家庭教育等非正常家庭生态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压实家长的主体责任,在反校园欺凌专项立法时,明确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强化家长的监护与教管责任,当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应及时给予干预,采取必要法律措施。进一步拓展防治学生欺凌防治外延,推动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同频共振,法律、教育、监管、制度同向发力,公安、社区、学校、监护人之间紧密联动,建立校园、社区全覆盖的学生欺凌预警、巡逻、教育、管控机制。建立青少年欺凌举报与救助中心,推动学生欺凌早期识别、早期防治,共同系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护“安全带”,筑牢学生欺凌防治“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