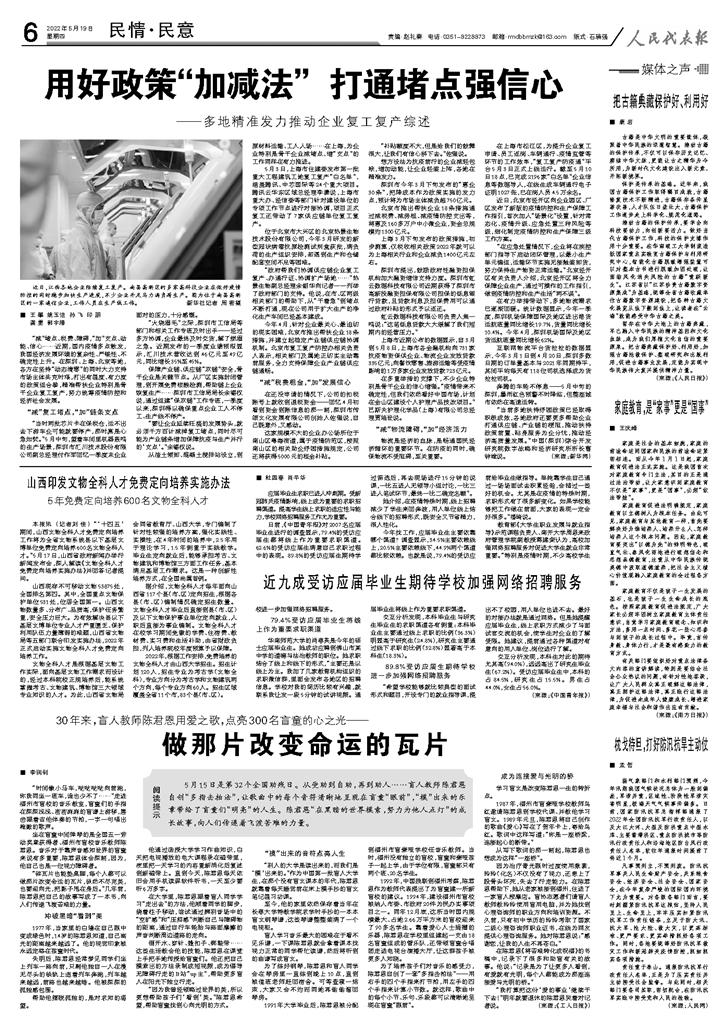■ 李润钊
“时间像小马车,哒哒哒哒向前跑,你我同坐一班车,谁也少不了……”走进福州市盲校的音乐教室,盲童们的手指在深深浅浅、密密麻麻的盲谱上游移,唇齿跟着吉他伴奏的节拍,一字一句唱出稚嫩的歌声。
坐在盲童中间弹琴的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州市盲校音乐教师陈君恩。音乐对于靠声音感知世界的盲童来说有多重要,陈君恩体会深刻,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视力障碍者。
“碎瓦片也能垫桌脚,每个人都可以做那片改变命运的瓦片,纵然不尽完美,也要迎向光,把影子甩在身后。”几年前,陈君恩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向人们传递飞渡苦难的力量。
冲破黑暗“看到”美
1977年,当家里的白墙在自己眼中变成绿色时,14岁的陈君恩知道,自己离光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他的视觉印象被永远定格在孩童时代。
失明后,陈君恩经常梦见同学们坐上列车一路向前,只剩他独自一人在漫无尽头的铁轨上追着列车奔跑,列车越来越远,前路也越来越暗。他被深深的孤独感包围。
帮助他摆脱孤独的,是对求知的渴望。
他通过函授大学学习作曲知识,白天把电视播放的电大课程录在磁带里,夜里把一天学习的内容重新消化后复述到新磁带上。直到今天,陈君恩每天依旧会用手机读屏软件听书,一天至少要听6万多字。
在大学里,陈君恩跟着盲人同学学习“走出去”的方法,他顺着同学的脚步,绕着柱子移动,尝试通过辨别音场中的“空旷感”和“压抑感”判断自己与障碍物的距离,通过自行车轮胎与路面摩擦的声音判断周边道路的走向。
倒开水、穿针、缝扣子、绑鞋带……这些生活教会他的技能,陈君恩在课堂上手把手地传授给盲童们。他还把自己摸索出的方法录制成短视频,成为倡导无障碍行走的B站“up主”,帮助更多盲人在阳光下独立行走。
“因为我曾经领略过世界的美,所以更想帮助孩子们‘看到’美。”陈君恩希望,帮助盲童找到心向光明的方式。
“摸”出来的音符点亮人生
“别人的大学是读出来的,而我们是‘摸’出来的。”作为中国第一批盲人大学生,在那个没有盲文课本的年代,陈君恩就靠着每天睡觉前在床上摸手抄的盲文笔记温习功课。
至今,他的家里依然保存着当年在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求学时手抄的一本本盲文钢琴谱,这些琴谱整整装满了一个电视柜。
盲人学习音乐最大的困难在于看不见乐谱,一下课陈君恩就会拿着课本找视力正常的同学帮忙读谱,然后将听到的曲谱写成盲文。
为了练好钢琴,陈君恩和盲人同学会在琴房里一直练到晚上10点,直到被值班老师赶回宿舍。可等查寝一结束,大家又会不约而同地再偷偷溜回琴房。
1991年大学毕业后,陈君恩被分配到福州市盲聋哑学校任音乐教师。当时,福州没有独立的盲校,盲童和聋哑孩子一起上学,由于学位有限,盲童部只有两个班、20名学生。
1992年,中国残联到福州考察,陈君恩作为教师代表提出了为盲童建一所新盲校的建议。1994年,建设福州市盲校被纳入市委、市政府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同年12月底,这所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占地2.66万平方米的盲校迎来了90多名学生。靠着爱心人士捐赠的乐器,陈君恩在学校里组建起一支由18名盲童组成的管乐队,还带领盲童合唱团走进电视台演播大厅,让这群孩子被更多人知晓。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音乐的感受力,陈君恩自创了一套“多指击拍法”——用右手的四个手指来打节拍,用左手的四个手指来计算小节数。就这样,歌曲中的每个小节、乐句、乐段都可以清晰地呈现在盲童“眼前”。
成为连接爱与光明的桥
学习盲文是改变陈君恩一生的转折点。
1987年,福州市盲聋哑学校教师乌红邀请陈君恩到学校代课、并教他学习盲文。1989年元旦,陈君恩将自己创作的歌曲《爱心》写在了贺年卡上,寄给乌红。歌词中这样写道:“你是一座桥梁,连接起心的断带。”
从写下歌词的那一刻起,陈君恩也想成为这样“一座桥”。
因为治疗青光眼时过度使用激素,玲玲(化名)不仅没有了视力,还患上了股骨头坏死,失去了行走能力。在陈君恩帮助下,她从老家被接到福州,住进了一家盲人按摩店。盲协志愿者们请盲人教师教玲玲使用盲用电脑,并为她找到心理咨询师的职业方向和培训资源。不久前,只有初中学历的玲玲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在线为网友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她对陈君恩说:“感谢您,让我的人生不再苍白。”
在陈君恩《将苦难转化成祝福》的书稿中,记录下了很多和助盲有关的故事。他说:“记录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有爱就有光明,每个人都能成为那座连接爱与光明的桥。”
“我打算把这份‘爱的事业’继续干下去!”明年就要退休的陈君恩笑着对记者说。(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