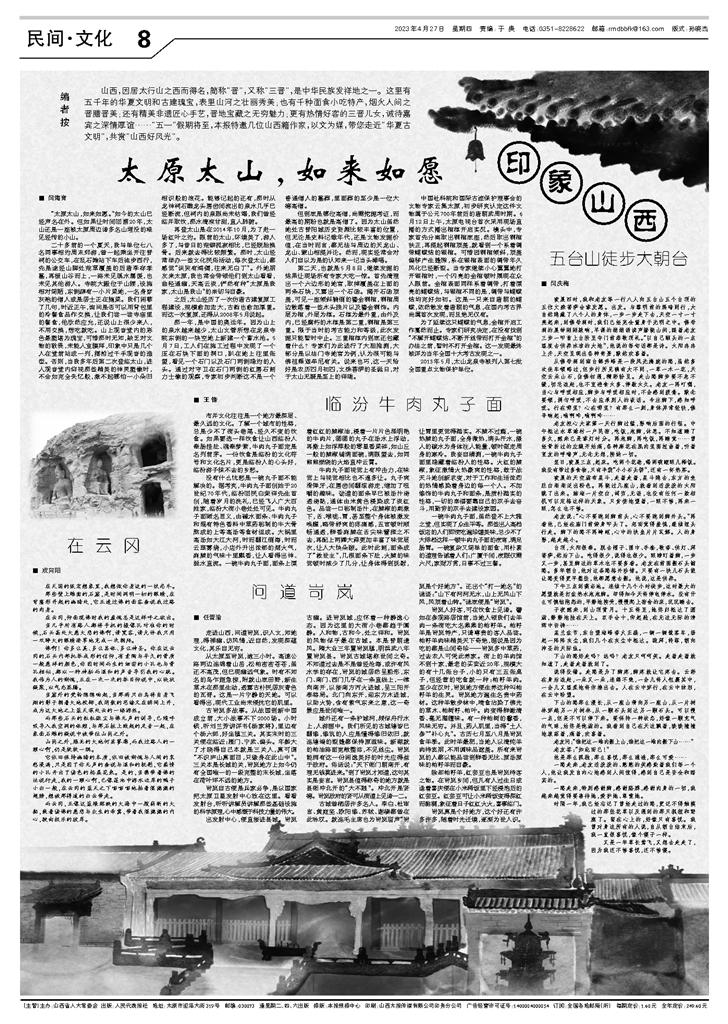■ 闫海育
“太原太山,如来如愿。”如今的太山已经声名在外。但如果让时间回溯20年,太山还是一座被太原周边诸多名山埋没的难见经传的小山。
二十多前的一个夏天,我与单位七八名同事相约周末郊游,曾一起乘坐开往晋祠的公交车,在乱石滩站下车后徒步西行,先是途经山脚处荒草覆盖的后唐李存孝墓,再援山谷而上,一路未见溪水潺湲,也未见其他游人。寺院大殿位于山腰,设施相对简陋,东侧辟有一小片菜地,一名身穿灰袍的僧人或是居士正在摘菜。我们闲聊了几句,时近正午,询问是否可以用背包里的冷餐食品作交换,让我们尝一尝寺庙里的餐食,他欣然应允,还说山上很少来人,不用交换,想吃就吃。山上观音堂内的彩色悬塑堪为瑰宝,可惜那时无知,缺乏对文物的敬畏,未能入室膜拜,印象中只是几个人在堂前站成一列,摆拍过千手观音的造型。否则,当我多年后第二次登临太山,进入观音堂内仰视那些精美的神灵塑像时,不会如完全失忆般,激不起哪怕一小朵旧相识般的浪花。能够记起的还有,那时从龙神祠石雕龙头唇齿间流出的泉水几乎已经断流,但祠内的泉眼尚未枯竭,我们曾经临井取饮,那水清凉甘甜,直入肺腑。
再登太山是在2014年10月,为了赴一场红叶之约。眼前的太山,环境美了,游人多了,与昔日的荒僻孤寂相比,已经脱胎换骨。后来就去得比较频繁。那时,太山经常举办一些文化民俗活动,每次登太山,都感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外地朋友来太原,我也常会带领他们到太山看看,曲径通幽,天高云淡,俨然有种“太原是我家,太山是我山”的亲切与自豪。
之后,太山经历了一次仿唐古建复原工程建设,规模愈加宏大,古韵也愈加厚重。而这一次复原,还得从2008年5月说起。
那一年,是中国的奥运年。因为山上的泉水越来越少,太山文管所想在龙泉寺院东侧的一块空地上新建一个蓄水池。5月7日,工人们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压在石块下面的洞口,趴在地上往里张望,看见一个石门以及石门两侧隐约的人头。通过对守卫在石门两侧的红唇石刻力士像的观察,专家初步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僧人的墓葬,里面葬的至少是一位大德高僧。
但到底是哪位高僧,尚需挖掘考证,而最高的期盼也就是高僧了。因为太山虽然地处古晋阳城历史资源比较丰富的位置,但无论是史料记载年代,还是文物发掘价值,在当时而言,都无法与周边的天龙山、龙山、蒙山相提并论。然而,现实经常会对人们自以为是的认知来一记当头棒喝。
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继续发掘的结果让现场所有专家大吃一惊。首先清理出一个六边形的地宫,取掉覆盖在上面的两条石块,又露出一个石函。揭开石函顶盖,可见一座倾斜躺倒的鎏金铜棺,铜棺周边散落着一些木头残片以及鎏金铜饰。内层为棺,外层为椁。石椁为最外重,由外及内,已经腐朽的木椁是第二重,铜棺是第三重。限于当时的考古能力和等级,此次发掘只能暂时中止。三重棺椁内到底还包藏着什么?专家们为此进行了大胆推测,大部分是以法门寺地宫为例,认为很可能与佛祖释迦牟尼有关。说来也巧,这一天恰好是农历四月初四,文殊菩萨的圣诞日,对于太山无疑是至上的祥瑞。
中国社科院和国际古迹保护理事会的文物专家云集太原,初步研究认定这件文物属于公元700年前后的唐朝武周时期。6月12日上午,太原电视台首次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棺椁开启实况。镜头中,专家首先分离取出铜棺底座,然后取出铜棺扶正,再提起铜棺顶盖,就看到一个系着绸带蝴蝶结的银棺。可惜因铜棺倾斜,顶盖偏移产生缝隙,系在银棺表面的绸带年久风化已经断裂。当专家继续小心翼翼地打开银棺时,一个闪亮的金棺顿时展现在众人眼前。金棺表面同样系着绸带,打着漂亮的蝴蝶结,与银棺不同的是,绸带与蝴蝶结均完好如初。这是一只来自唐朝的蝴蝶,依然散发着唐朝的气息,在国内考古界尚属首次发现,而且绝无仅有。
为了延续这只蝴蝶的气息,金棺开启工作戛然而止。专家们研究决定,在没有找到“不解开蝴蝶结、不断开丝带而打开金棺”的办法之前,暂时不打开金棺。这一发现最终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13年5月,太山龙泉寺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