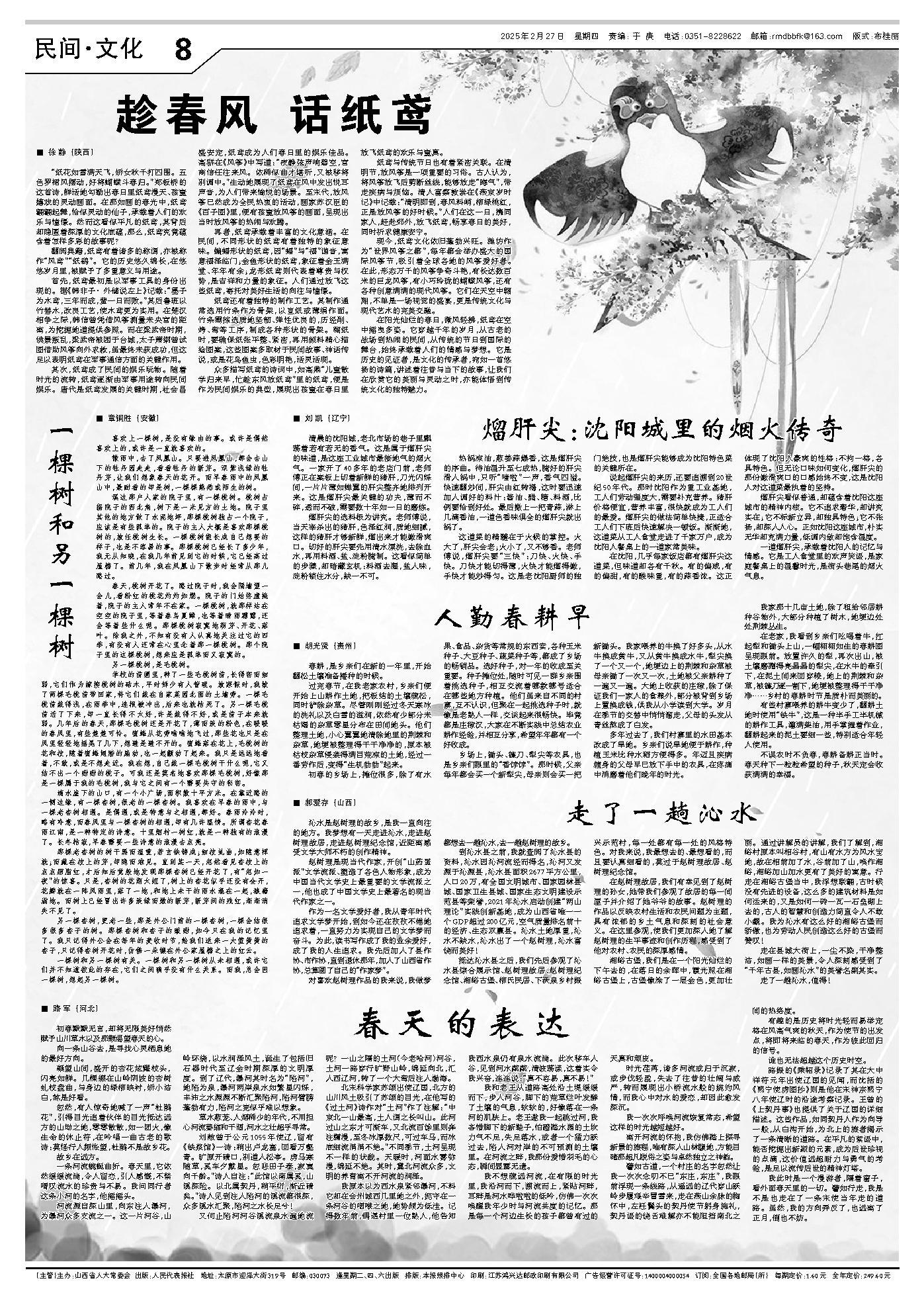■ 路 军 (河北)
初春默默无言,却将无限美好悄然赋予山川草木以及那颗渴望春天的心。
向一条山谷去,是寻找心灵栖息地的最好方向。
凝望山间,盛开的杏花炫耀枝头,闪亮如鲜。几棵缀在山岭阴坡的杏树虬枝盘曲,与身边的绿柳映衬,娇小洁白,煞是好看。
忽然,有人惊奇地喊了一声“杜鹃花”,引得目光追着伙伴的目光抵达远方的山坳之地,零零散散,如一团火,像生命的休止符,在吟唱一曲古老的歌诗:莫怪行人频怅望,杜鹃不是故乡花。
故乡在远方。
一条河流蜿蜒曲折。春天里,它依然缓缓流淌,令人留恋,引人感慨,不禁喟叹流水的珍贵与不易。我问同行者这条小河的名字,他摇摇头。
河流源自深山里,向东注入瀑河,为瀑河众多支流之一。这一片河谷,山岭环绕,以水润泽风土,诞生了包括旧石器时代至辽金时期深厚的文明厚度。到了辽代,瀑河其时名为“陷河”,地陷为泉,瀑河两岸泉水如繁星闪烁,丰沛之水源源不断汇聚陷河,陷河臂膀蓬勃有力,陷河之宽似乎难以想象。
草木葱茏、人烟稀少的年代,不用担心河流萎缩和干涸,河水之壮超乎寻常。
刘敞曾于公元1055年使辽,留有《铁浆馆》一诗:稍出卢龙塞,回看万壑青。旷原开碛口,别道入松亭。虏马寒随草,奚车夕戴星。忽悲田子泰,寂寞向千龄。”诗人自注:“此馆以南属奚,山溪深险。以北属契丹,稍平衍,渐近碛矣。”诗人见到注入陷河的溪流都很深,众多溪水汇聚,陷河之水长足兮!
又何止陷河河谷溪流泉水遍地流呢?一山之隔的土河(今老哈河)河谷,土河一路穿行旷野山岭,绵延向北,汇入西辽河,转了一个大弯后注入渤海。
北宋科学家苏颂出使辽国,北方的山川风土吸引了苏颂的目光,在他写的《过土河》诗作对“土河”作了注解:“中京北一山最高,土人谓之长叫山。此河过山之东才可渐车,又北流百馀里则奔注瀰漫,至冬冰厚数尺,可过车马,而冰底细流涓涓不绝。”不同季节,土河呈现不一样的状貌。天暖时,河面水雾弥漫,绵延不绝。其时,冀北河流众多,文明的养育离不开河流的润泽。
我原本以为西水泉紧邻瀑河,不料它却在会州城西几里地之外,扼守在一条河谷的咽喉之地,地势颇为低洼。记得数年前,偶遇村里一位熟人,他告知我西水泉仍有泉水流淌。此次移车入谷,见到河水粼粼,清波荡漾,这着实令我兴奋,连连说:“真不容易,真不易!”
我和老王从道路高处沿土堤缓缓而下,步入河谷,脚下的荒草烂叶发酵了土壤的气息,软软的,好像落在一条河的肌肤上。老王邀我一起跳过河,我吝惜脚下的新鞋子,怕蹬踏水湄的土坎力气不足,失足落水,或者一个猛力跃过去,陷入河对岸的不可预测的土壤里。在河流之畔,我那份爱惜羽毛的心态,瞬间显露无遗。
我不想疏远河流,在有限的时光里,我沿河而下,溯流而上,紧贴河畔,耳畔是河水哗啦啦的低吟,仿佛一次次唤醒我年少时与河流共度的记忆。那是每一个河边生长的孩子都曾有过的天真和顽皮。
时光荏苒,诸多河流或归于沉寂,或步伐轻盈,失去了往昔的壮阔与威严,转而展现出小桥流水般的婉约风情,而我心中对水的爱恋,却因此愈发深沉。
我一次次呼唤河流恢复常态,希望这样的时光越短越好。
离开河流的怀抱,我仿佛踏上探寻新景的旅程,唯有深入山林腹地,方能目睹那超凡脱俗之姿与卓然独立之神韵。
譬如古道,一个村庄的名字忽然让我一次次念叨不已“东庄,东庄”,我眼前浮现一条线路,从遥远的辽代穿山跃岭步履艰辛冒雪来,走在燕山余脉的胸怀中,左衽鬓头的契丹使节躬身施礼,契丹语的饶舌难解亦不能阻挡南北之间的热络度。
有趣的是历史将时光轻而易举定格在风高气爽的秋天,作为使节的出发点,将即将来临的春天,作为彼此回归的信号。
谁也无法超越这个历史时空。
路振的《乘轺录》记录了其在大中祥符元年出使辽国的见闻,而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则是他在宋神宗熙宁八年使辽时的沿途考察记录。王曾的《上契丹事》也提供了关于辽国的详细描述。这些作品,如同契丹人作为向导一般,从白沟开始,为北上的旅者揭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在平凡的絮语中,能否挖掘出新颖的元素,成为后世珍视的点滴,这价值远超耐力与勇气的考验,是足以流传后世的精神灯塔。
我此时是一个漫游者,隔着窗子,看外面春天里的一切。譬如行走,我是不是也走在了一条宋使当年走的道路。虽然,我的方向弄反了,也远离了正月,倒也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