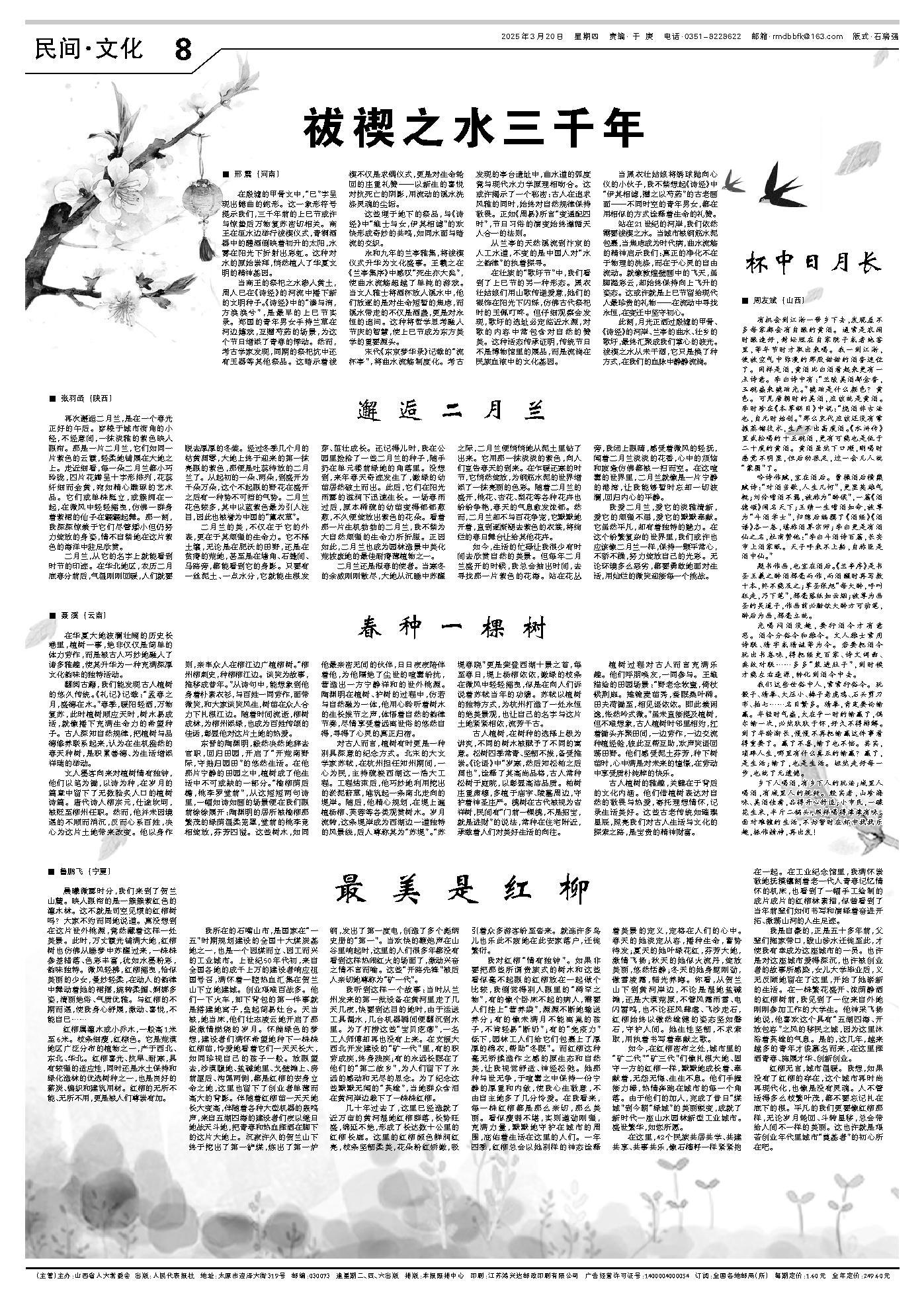■ 邢 震 (河南)
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巳”字呈现出蜷曲的蛇形。这一象形符号提示我们,三千年前的上巳节或许与惊蛰后万物复苏密切相关。商王在洹水边举行祓禊仪式,青铜酒器中的醴酒倒映着初升的太阳,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这种对水的原始崇拜,悄然植入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基因。
当商王的祭祀之水渗入黄土,周人已在《诗经》的河流中播下新的文明种子。《诗经》中的“溱与洧,方涣涣兮”,是最早的上巳节实录。郑国的青年男女手持兰草在河边嬉戏,互赠芍药的场景,为这个节日增添了青春的悸动。然而,考古学家发现,同期的祭祀坑中还有玉器等其他祭品。这暗示着祓禊不仅是求偶仪式,更是对生命轮回的庄重礼赞——以新生的喜悦对抗死亡的阴影,用流动的溪水洗涤灵魂的尘垢。
这些埋于地下的祭品,与《诗经》中“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欢快形成奇妙的共鸣,如同水面与暗流的交织。
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将祓禊仪式升华为文化盛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死生亦大矣”,使曲水流觞超越了单纯的游戏。当文人雅士将酒杯放入溪水中,他们放逐的是对生命短暂的焦虑,而溪水带走的不仅是酒盏,更是对永恒的追问。这种将哲学思考融入节庆的智慧,使上巳节成为东方美学的重要源头。
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流杯亭”,将曲水流觞制度化。考古发现的亭台遗址中,曲水道的弧度竟与现代水力学原理相吻合。这或许揭示了一个秘密:古人在追求风雅的同时,始终对自然规律保持敬畏。正如《周易》所言“变通配四时”,节日习俗的演变始终遵循天人合一的法则。
从兰亭的天然溪流到汴京的人工水道,不变的是中国人对“水之韵律”的执着探寻。
在壮族的“歌圩节”中,我们看到了上巳节的另一种形态。黑衣壮姑娘们用山歌传递爱意,她们的银饰在阳光下闪烁,仿佛古代祭祀时的玉佩叮咚。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歌圩的选址必定临近水源,对歌的内容中常包含对自然的赞美。这种活态传承证明,传统节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当黑衣壮姑娘将绣球抛向心仪的小伙子,我不禁想起《诗经》中“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古老画面——不同时空的青年男女,都在用相似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礼赞。
站在21世纪的河岸,我们依然需要祓禊之水。当城市被钢筋水泥包裹,当焦虑成为时代病,曲水流觞的精神启示我们:真正的净化不在于物理的洗涤,而在于心灵的自由流动。就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虽脚踏彩云,却始终保持向上飞升的姿态。这或许就是上巳节留给现代人最珍贵的礼物——在流动中寻找永恒,在变迁中坚守初心。
此刻,月光正洒过殷墟的甲骨、《诗经》的河岸、兰亭的曲水、壮乡的歌圩,最终汇聚成我们掌心的波光。祓禊之水从未干涸,它只是换了种方式,在我们的血脉中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