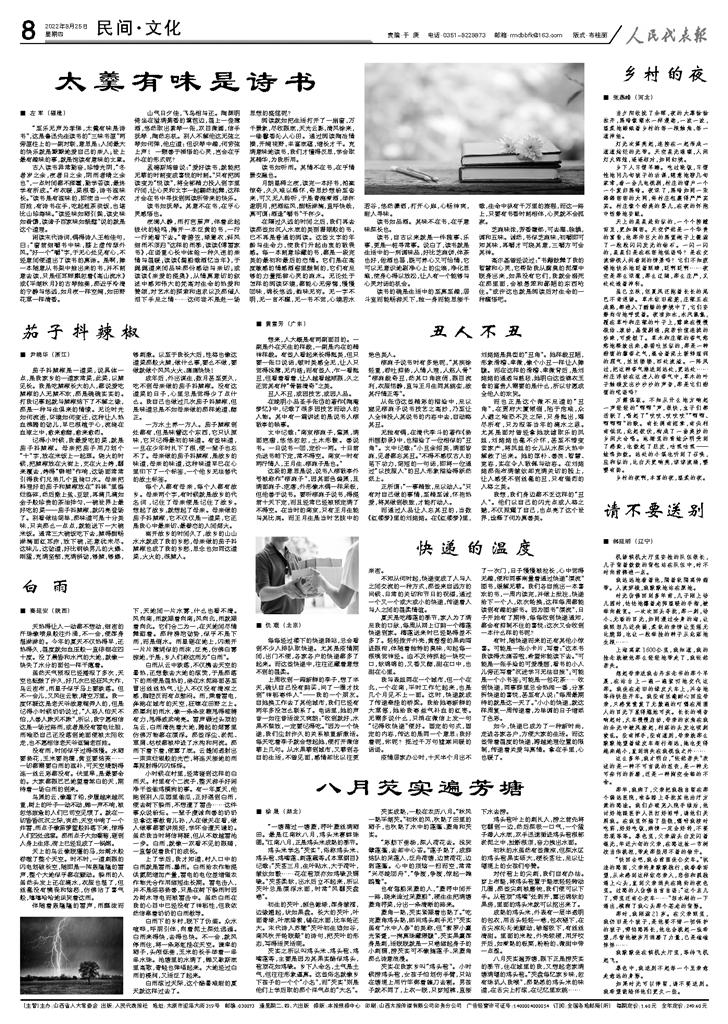■ 徐 晟 (湖北)
“一塘蒲过一塘菱,荇叶菱丝满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蚌珠圆。”江南八月,正是鸡头米成熟的季节。
鸡头米学名“芡实”,俗称鸡头米、鸡头苞、鸡嘴莲、刺莲藕等。《本草纲目》记载:“芡茎三月,生叶贴水,大于荷叶,皱纹如彀……花在苞顶亦如鸡喙及猬喙。”芡茎柔软,出水后立不起来,所以芡叶总是漂浮水面,时常“风翻芡盘卷”。
初生的芡叶,颜色嫩绿,浑身皱褶,边缘翘起,状如果盘。长大的芡叶,叶面青绿,叶底绛紫,铺在水面,比车轮还大。宋代诗人苏辙“芡叶初生绉如谷,南风吹开轮脱毂”的诗句,把芡叶的形态,写得活灵活现。
芡实之所以叫鸡头米、鸡头苞、鸡嘴莲等,主要是因为其果实酷似鸡头,苞顶花如鸡喙。乡下人命名,土气是土气,但往往形象逼真。这些俗名就像乡下孩子的一个个“小名”,而“芡实”则是他们上学后取的那个洋气点的“大名”。
芡实成熟,一般在农历八月。“秋风一熟平湖芡。”初秋的风,吹熟了田里的稻子,也吹熟了水中的莲蓬、菱角和芡实。
“彩舫下垂杨,深入荷花去。浅笑擘莲蓬,去却中心苦。”莲子熟了,成群结队的采莲人,泛舟荷塘,边赏荷花,边剥莲蓬。心中的烦恼一扫而空,常常“兴尽晚回舟”,“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也有驾船采菱的人,“菱荇中间开一路,晓来谁过采菱船”,硬生生把满塘菱角荇菜,分出一条清晰的路来。
菱角一熟,芡实紧跟着也熟了。“吃完菱角鸡头熟,郎问鸡头刺手无?”芡实虽有“水中人参”的美称,但“紫罗小囊光紧蹙,一掬真珠藏猥腹”,芡实果囊浑身是刺,活脱脱就是一只卷缩起身子的小刺猬,捞芡实可不像摘莲子、采菱角那么诗意浪漫。
芡实在我家乡叫“鸡头苞”。小时候捞鸡头苞,女孩子怕划伤手臂,只站在塘堤上用竹竿绑着镰刀去割。男孩子就不同了,上衣一脱,只穿短裤,直接下水去捞。
鸡头苞叶上的刺扎人,捞之前先将它翻到一边,然后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潜入水底,双手迅速插进鸡头苞根部淤泥之中,扯断根须,奋力拽出水面。
初秋的水虽然有些微凉,但深水区的鸡头苞果实硕大,梗长茎壮,足以让堰堤上的女孩们夸赞。
对付苞上的尖刺,我们自有办法。穿上布鞋,将鸡头苞置于鞋底轻轻转动几圈,那些尖刺被磨钝,我们便可以下手。从苞顶“鸡嘴”处剥开,露出绵软的果房,里面的鸡头米就可以抠出来了。
成熟的鸡头米,外表有一层半透明的包衣,用舌头轻轻一卷,包衣褪下,在舌尖凉沁沁地颤动,哧溜吸下,有丝丝清甜。里面的米粒,外壳较硬,用牙咬开后,如煮熟的板栗,粉粉的、微甜中带一点涩。
八月芡实遍芳塘,眼下正是捞芡实的季节,住在城里的我,又想起老家满塘满堰的鸡头苞。“芡盘每忆家乡味,忽有珠玑入我喉”,那熟悉的鸡头米的味道,在舌尖上打滚,在记忆里欢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