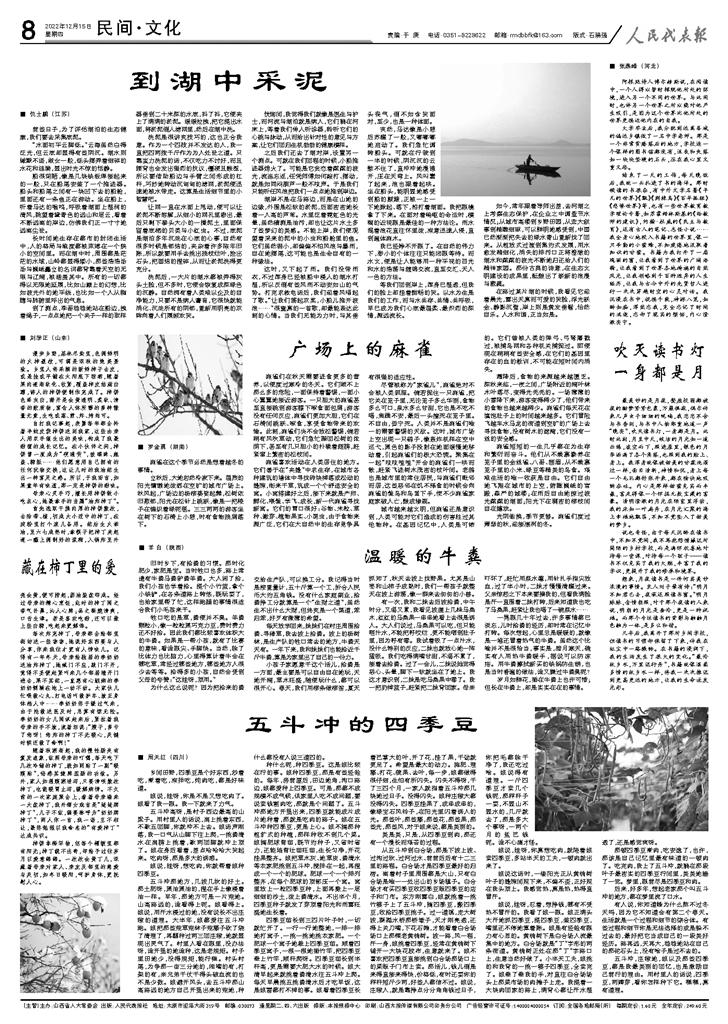■ 仇士鹏 (江苏)
前些日子,为了评估湖泊的生态健康,我们要去采集底泥。
“水面初平云脚低。”云海虽然白得泛光,但云底却显得有些阴沉。湖水则缄默不语,淑女一般,低头摆弄着细碎的水花和涟漪,显出时光不惊的恬静。
船很简陋,像是几块铁板焊接起来的一般,只在船尾安装了一个推进器。船头和船尾之间有一块凹下去的船舱,里面还有一条鱼正在游动。坐在船上,听着马达的嗡鸣,呼吸着湖面上湿润的清风,眺望着黛青色的远山和层云,看着不断远离的岸边,仿佛我们正一寸寸地远离尘世。
长时间地生存在都市的封闭生活中,人的格局与维度都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而在湖中时,周围都是茫茫的水域,山岭都显得矮小,那些浩浩汤汤与巍峨矗立的名词都背靠着天空的无垠与辽阔,被涵盖其中。所有的一切都得以无限地延展,比如山巅上的幻想,比如波光外的地平线,也比如一个人从胸臆与肺腑里呼出的气息。
到了测点,李哥稳稳地站在船边,拽着绳子,一点点地把一个夹子一样的取样器垂到二十米深的水底,抖了抖,它便夹上了满满的淤泥。缓缓拉拽,把它提出水面,将淤泥倒入滤网里,然后在湖中洗。
洗泥是很讲究技巧的,这也正合我意。作为一个四肢并不发达的人,我一直把四两拨千斤作为为人处世之道。只靠蛮力洗泥的话,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腰背也会发出强烈的抗议,僵硬且酸涩,所以要借助船边与手臂之间形成的杠杆,巧妙地转动沉甸甸的滤网,淤泥便迅速地被水带走。这算是生活细节里的小智慧吧。
让网一直在水面上甩动,便可以让淤泥不断溶解,从细小的网孔里渗出,最后只剩下拳头大小的一撮泥土,里面保留着底栖的贝类与小红虫。不过,底泥是湖泊多年沉淀在心底的心事,自然有很多时候是郁结的,夹杂着许多陈年旧账,所以就要用手去挑出残枝烂叶,捡出石头,把固结的捏碎,从而让淤泥洗得更充分。
洗泥后,一大片的湖水都被弄得灰头土脸,但不多时,它便会恢复成深绿色的沉静。自然拥有着人类难以企及的自净能力,只要不是病入膏肓,它很快就能消化、沉淀所有的阴郁,重新用明亮的双眸向着人们展颜欢笑。
恍惚间,我觉得我们就像是医生与护士,而河流与湖泊就是病人,它们躺在河床上,等着我们伸入听诊器,聆听它们的心跳与脉动,从而给出针对性的意见与方案,让它们回归生机勃勃的健康模样。
之后我们还去了湖对岸,设置另一个测点。可就在我们回程的时候,小船推进器熄火了。可能是它贪恋着粼粼的波光,流连忘返,任凭师傅如何敲打、摆动,就是如同闷葫芦一般不吱声。于是我们只能听任风浪把我们一点点地推到岸边。
湖岸不是在马路边,而是在山地的边缘,外围是松软的淤泥,后面密密地长着一人高的芦苇。水里泛着霓虹色的光晕,虽然猜测是油污,却也让这片水土多了些梦幻的美感。不能上岸,我们便观望着采来的泥中的小虫和船舱里的鱼。它们虽然弱小,却偏偏不怕风浪与暴雨,自在地摆尾,这可能也是生命自有的一种缘法。
这时,又下起了雨。我们没带雨衣,不过浑身已经被船中浸入的湖水打湿,所以反倒有些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气势。打完求救电话后,我们迎着风唱起了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很童真的一首歌,却最能表达此刻的心情。当我们无能为力时,与其垂头丧气,倒不如含笑面对,至少,也是一种体面。
突然,马达像是小憩后苏醒了一般,又嘟嘟嘟地启动了。我们急忙调转船头。可就在行驶到一半的时候,阴沉沉的云憋不住了,直冲冲地漫漶开,压在天穹上。风叫嚣了起来,浪也跟着起哄。坐在船头,能明显地感受到船的颠簸,正被一上一下地掀起、落下,拍打着湖面。我把眼镜拿了下来。在面对着崎岖的命运时,模糊的近视眼是最佳的一种方法论。雨水混着浪花直往怀里泼,凉意迅速入侵,直到遍体麻木。
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在自然的伟力下,渺小的个体往往只能闭眼等待。而水文,便是让人能够用一种平视的目光和水的浩荡与缠绵交流,直至交汇、天人一色的方法。
等我们回到岸上,浑身已湿透,但我们的脸上却挂着酣畅的笑。以水为生是我们的工作,而与水共存、共情、共呼吸,早已成为我们心底最温柔、最炽烈的深情,源远流长。
如今,常年跟着导师出差,去河湖之上考察生态保护,在企业之中调查节水情况;从城市高楼到乡野田园,从宏大叙事到精雕细琢,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中国已然渐渐把失去的绿水青山重新找了回来。从粗放式过渡到集约式发展,用水愈发精细化,消失的排污口正将澄澈的湖水和粼粼的波光不断地归还给人们的精神家园。那份古典的诗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里,酝酿出了崭新的浪漫与葳蕤。
在路过某片湖的时候,我看见它迎着晨光,露出天真而可爱的笑脸,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岸上则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人水和谐,正当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