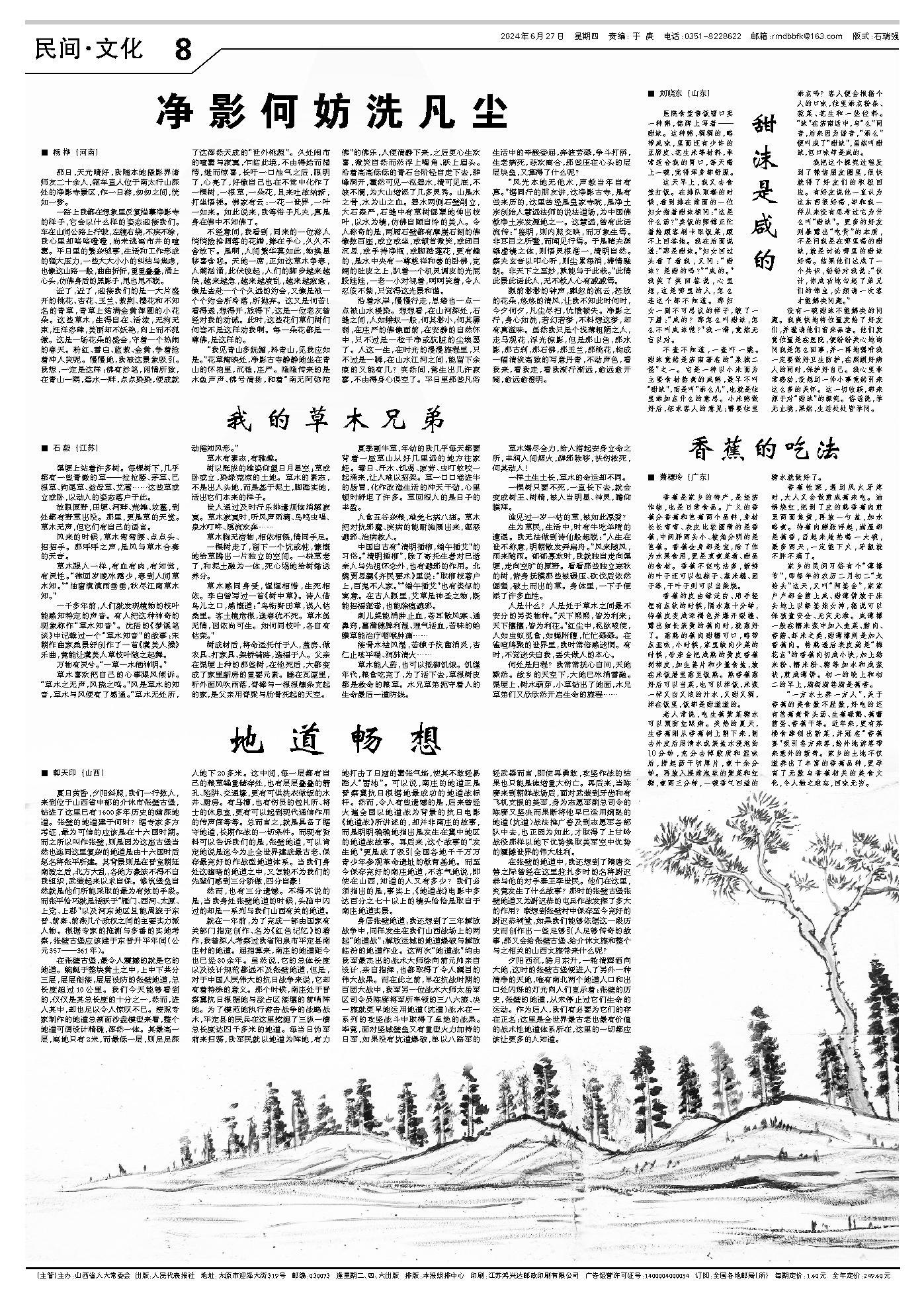■ 杨 桦 (河南)
那日,天光晴好,我随本地摄影界诸师友二十余人,驱车直入位于南太行山深处的净影寺景区,作一日游,匆匆之间,恍如一梦。
一路上我都在想象里反复描摹净影寺的样子,它会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我们。车在山间公路上行驶,左缠右绕,不疾不徐,我心里却咯咯噔噔,尚未逃离市井的喧嚣。平日里的繁杂琐事,生活和工作形成的强大压力,一些大大小小的纠结与焦虑,也像这山路一般,曲曲折折,重重叠叠,涌上心头,仿佛身后的黑影子,甩也甩不脱。
近了,近了,迎接我们的是一大片盛开的桃花、杏花、玉兰、紫荆、樱花和不知名的青草,青草上结满金黄浑圆的小花朵。这些草木,生得自在、活泼,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美丽却不妖艳,向上而不孤傲。这是一场花朵的盛会,守着一个热闹的春天。粉红、雪白、蓝紫、金黄,争着抢着冲人笑呢。慢慢地,我被这景象吸引。我想,一定是这样:佛有妙笔,闲情所致,在青山一隅,碧水一畔,点点染染,便成就了这浑然天成的“世外桃源”。久处闹市的喧嚣与寂寞,乍临此境,不由得始而错愕,继而惊喜,长吁一口浊气之后,眼明了,心亮了,好像自己也在不觉中化作了一棵树,一根草,一朵花,且来吐故纳新,打坐悟禅。佛家有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如此说来,我等俗子凡夫,真是身在佛中不知佛了。
不经意间,我看到,同来的一位游人悄悄捡拾凋落的花瓣,捧在手心,久久不舍放下。是啊,人间繁华莫如此,物换星移喜含悲。天地一席,正如这草木争春,人潮汹涌,此伏彼起,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急,越来越凌乱,越来越疲惫,像是去赴一个个久远的约会,又像是被一个个约会所冷落,所抛弃。这又是何苦!看得透,想得开,放得下,这是一位老友曾经对我的劝诫。此时,这些花们草们树们何尝不是这样劝我啊。每一朵花都是一尊佛,是这样的。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花草掩映处,净影古寺静静地坐在青山的怀抱里,沉稳,庄严。隐隐传来的是木鱼声声、佛号清扬,和着“南无阿弥陀佛”的佛乐,人便清静下来,之后更心生欢喜,微笑自然而然浮上嘴角、跃上眉头。沿着高高低低的青石台阶径自走下去,群峰洞开,霍然可见一泓碧水,清可见底,不波不澜,为大山增添了几多灵秀。山是水之骨,水为山之血。碧水两侧石壁削立,大石森严,石缝中有草树倔犟地伸出枝叶,以水为镜,仿佛自顾自怜的美人。令人称奇的是,两厢石壁都有摩崖石刻的佛像数百座,或立或坐,或颔首微笑,或闭目沉思,或手持净瓶,或脚踏莲花,更有趣的,是水中央有一尊慈祥和善的卧佛,宽阔的肚皮之上,趴着一个机灵调皮的光屁股娃娃,一老一小对视着,呵呵笑着,令人忍俊不禁,只觉得这光景和谐。
沿着水岸,慢慢行走,思绪也一点一点被山水浸染。想想看,在山河深处,石缝之间,人如蝼蚁一般,何其渺小,何其孱弱,在庄严的佛像面前,在安静的自然怀中,只不过是一粒干净或肮脏的尘埃罢了。人这一生,在时光的漫漫旅程里,只不过是一瞬,在山水江河之间,能留下余痕的又能有几?突然间,竟生出几许寂寥,不由得身心俱空了。平日里那些凡俗生活中的辛酸委屈,奔波劳碌,争斗打拼,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那些压在心头的层层块垒,又算得了什么呢?
“风光本地无他术,声教当年自有真。”据同行的朋友讲,这净影古寺,是有些来历的,这里曾经是皇家寺院,是净土宗创始人慧远法师的说法道场,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源地之一。这慧远,曾有此话流传:“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镜之体,则悟灵根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以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此情此景此话此人,无不教人心有戚戚焉。
眼前渺渺的钟声,飘忽的流云,怒放的花朵,悠悠的清风,让我不知此时何时,今夕何夕,凡尘尽扫,忧愤顿失。净影之行,身心如洗,若幻若梦,不料想这梦,却有真滋味。虽然我只是个浅薄粗陋之人,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是那山色,那水影,那古刹,那石佛,那玉兰,那桃花,构成一幅清淡高致的写意丹青,不动声色,看我来,看我走,看我渐行渐远,愈远愈开阔,愈远愈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