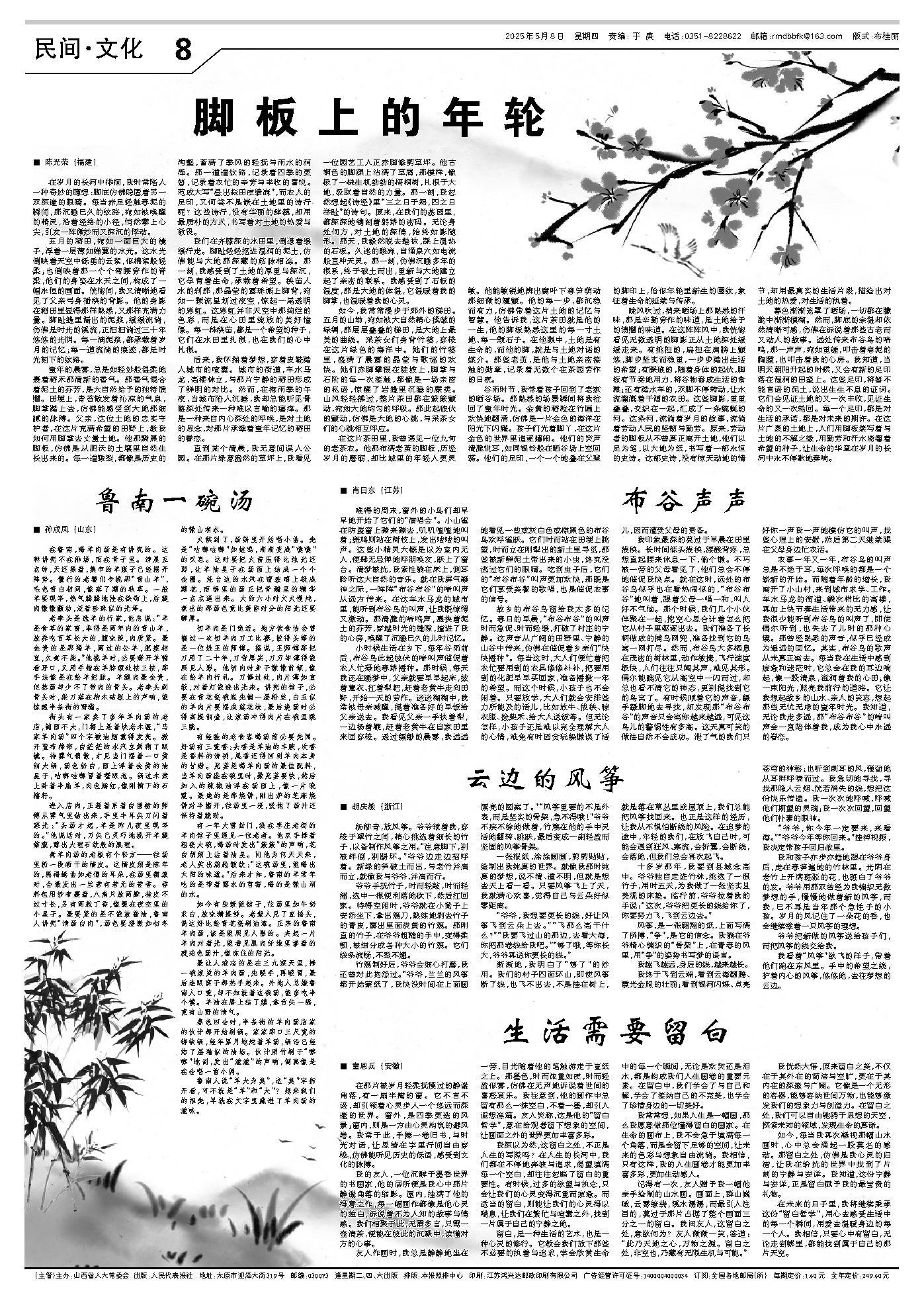■ 孙成凤 (山东)
在鲁南,喝羊肉汤是有讲究的。这种讲究不在排场,而在骨子里。清晨五点钟,天还黑着,集市的羊贩子已经摆开阵势。懂行的老饕们专挑那“青山羊”,毛色青白相间,像落了霜的秋草。一般羊要现宰,热气腾腾地挂在铁钩上,后腿肉微微颤动,泛着珍珠似的光泽。
老李头是选羊的行家,他总说:“羊是食草的家畜,非得是两年内的青山羊,放养吃百草长大的,膻味淡,肉质紧。最金贵的是那羯羊,阉过的公羊,肥瘦相宜,久煮不柴。”他挑羊时,必要掰开羊嘴看牙口,又用手指在羊脖颈处按三按,那手法像是在给羊把脉。羊腿肉最金贵,但熬汤却少不了带肉的骨头。老李头剁骨头时,柴刀落在柳木砧板上的声响,能惊醒半条街的野猫。
街头有一家卖了多年羊肉汤的老店,铺面不大,门楣上悬着块老木匾,“马家羊肉汤”四个字被油烟熏得发亮。掀开蓝布棉帘,白茫茫的水汽立刻糊了眼镜。待雾气稍散,才见当门摆着一口黄铜大锅,汤色奶白,面上浮着金黄的油星子,咕嘟咕嘟冒着蟹眼泡。锅边木案上卧着半扇羊,肉色嫣红,像刚摘下的石榴籽。
进入店内,正遇着系着白围裙的师傅从雾气里钻出来,手里牛耳尖刀闪着寒光:“头汤才起,羊是昨儿夜里现宰的。”他说话时,刀尖已灵巧地挑开羊腿筋膜,露出大理石纹般的肌理。
煮羊肉汤的老板有个秘方——往汤里扔一段晒干的橘皮。这橘皮须是陈年的,黑褐蜷曲如老僧的耳朵,在汤里翻滚时,会散发出一丝若有若无的苦香。香料包用纱布裹着,八角只放两瓣,桂皮不过寸长,另有两粒丁香,像缀在夜空里的小星子。最要紧的是不能放酱油,鲁南人讲究“清汤白肉”,汤色要澄澈如初冬的微山湖水。
火候到了,汤锅里开始唱小曲。先是“咕嘟咕嘟”如蛙鸣,渐渐变成“噗噗”的叹息。这时要把火苗压得比烛光还弱,让羊油星子在汤面上结成一个个金圈。灶台边的水汽在窗玻璃上凝成霜花,而锅里的汤正把骨髓里的精华一点点逼出来。大约六小时文火慢炖,煮出的那汤色竟比黄昏时分的阳光还要醇厚。
切羊肉是门绝活。地方饮食协会曾搞过一次切羊肉刀工比赛,拔得头筹的是一位姓王的师傅。据说,王师傅那把刀用了二十年,刀背厚实,刀刃却薄得能照见人影。他切肉时身子微微前倾,像在给羊肉行礼。刀锋过处,肉片薄如宣纸,对着灯能透出光来。讲究的馆子,必要在青花瓷碗底先铺一层粉丝,白玉似的羊肉片要摆成莲花状,最后浇汤时必得高提铜壶,让滚汤冲得肉片在碗里跳三跳。
有经验的老食客喝汤前必要先闻。好汤有三重香:头香是羊油的丰腴,次香是香料的清冽,尾香还得回到羊肉本身的甘甜。芫荽是喝羊肉汤的最佳配料,当羊肉汤盛在碗里时,撒芫荽要快,然后加入的辣椒油浮在汤面上,像一片晚霞。最绝的是那烧饼,刚出炉的芝麻烧饼对半撕开,往汤里一浸,吸饱了汤汁还保持着脆劲。
有一年大雪封门,我在枣庄老街的羊肉馆子里遇见一位老者。他双手捧着粗瓷大碗,喝汤时发出“簌簌”的声响,花白胡须上沾着油星。问他为何天天来,老人笑出满脸皱纹:“这碗汤里,能喝出太阳的味道。”后来才知,鲁南的羊常年吃的是带着露水的苜蓿,喝的是微山湖的水。
如今有些新派馆子,往汤里加牛奶求白,放味精提鲜。老辈人见了直摇头,说这好比给青花瓷刷油漆。正宗的鲁南羊肉汤,该是能照见人影的。夹起一片羊肉对着光,能看见肌肉纤维里渗着的琥珀色汤汁,像冻住的阳光。
最让人难忘的是在三九寒天里,捧一碗滚烫的羊肉汤,先暖手,再暖胃,最后连眼窝子都热乎起来。外地人总嫌鲁南人口重,却不知就着这碗汤,能多吃半个馍。羊油在唇上结了膜,拿舌尖一舔,竟有山野的清气。
暮色四合时,半条街的羊肉汤店家的伙计都开始刷锅。家家那口三尺宽的铸铁锅,经年累月地炖着羊汤,锅沿已经结了层釉似的油垢。伙计用竹刷子“嚓嚓”地刮,发出“滋滋”的声响,倒真像是在合唱一首小调。
鲁南人说“羊大为美”,这“美”字拆开看,可不就是“羊”和“大”?想来我们的祖先,早就在文字里藏进了羊肉汤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