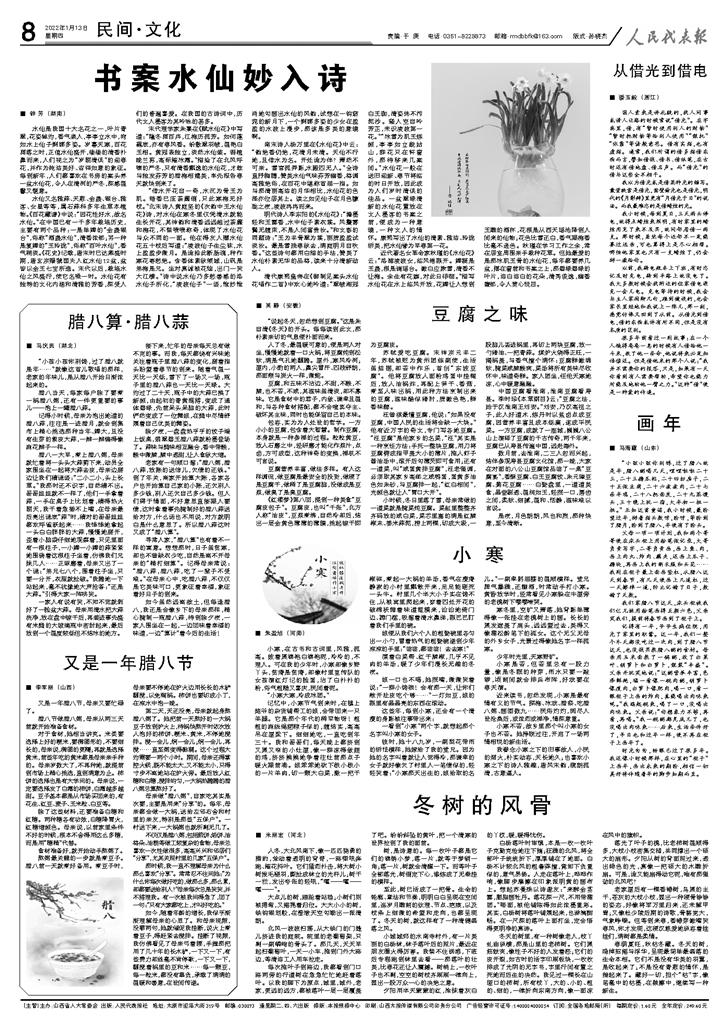■ 吴 静 (安徽)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这是朱自清《冬天》的开头。每每读到此文,那朴素亲切的气息便扑面而来。
入了冬,最温暖可意的,便是两人对坐,慢慢地就着一口火锅,将豆腐炖到松软,满是气孔地翻腾。屋外,寒风冷冽;屋内,小酌的两人,鼻尖冒汗、四肢舒朗,那面颊与炭火一样,微酡。
豆腐,和五味不沾边,不甜,不酸,不辣,也不苦,不咸,其滋味虽清淡,却不寡味。它是食材中的君子,内敛、谦卑且温和,与各种食材搭配,都不会喧宾夺主、破坏其主味,同时也能保留自己的本味。
包容,实为为人处世的哲学。一方小小的豆腐,包含着大智慧。制作豆腐,本身就是一种参禅的过程。粒粒黄豆,放入石磨之中,经研磨才能化作浆汁,点卤,方可成型,这种神奇的变换,禅机不可言说。
豆腐营养丰富,做法多样。有人这样调侃,做豆腐是最安全的投资,做硬了是豆腐干,做稀了是豆腐脑,没做成是豆浆,做臭了是臭豆腐。
《红楼梦》第八回,提到一种美食“豆腐皮包子”。豆腐皮,也叫“千张”,北方人称“油皮”,豆浆煮沸,自然冷却后,结出一层金黄色薄薄的薄膜,挑起晾干即为豆腐皮。
苏轼爱吃豆腐。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生活虽拮据,却苦中作乐,首创“东坡豆腐”。他将豆腐放入面粉鸡蛋中挂糊后,放入油锅炸,再配上笋干、香菇,煮至入味出锅,用此种方法烹制出来的豆腐,滋味酷似猪肘,质嫩色艳,鲜香味醇。
汪曾祺最懂豆腐,他说:“如果没有豆腐,中国人民的生活将会缺一大块。” 他有近万字的奇文,专门写各地豆腐。“汪豆腐”是他家乡的名菜,“汪”其实是一种烹饪方法:手托一整块豆腐,用刀将豆腐劈成指甲盖大小的薄片,推入虾子酱油汤中,滚开后勾薄芡即可食用;还有一道菜,叫“咸蛋黄拌豆腐”,汪老强调,必须取其家乡高邮之咸鸭蛋,蛋黄多油色如朱砂,与豆腐拌一起,“红白相间”,光颜色就让人“胃口大开”。
小时候,冬日里落了雪,母亲常做的一道菜就是腌菜炖豆腐。菜缸里整整齐齐码放的咸白菜,菜芯里塞的满是红辣椒末、姜米蒜泥,捞上两棵,切成大段,一股脑儿丢进锅里,再切上两块豆腐,放一勺猪油、一把青蒜。煤炉火烧得正旺,一揭锅盖,与香气撞个满怀:豆腐鲜嫩绵软,腌菜咸辣酸爽,菜汤将所有美味尽收怀中,味道奇鲜。家人团坐,任他天寒地冻,心中暖意融融。
中国豆腐看淮南,淮南豆腐看寿县。李时珍《本草纲目》云:“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刘安,乃汉高祖之子,此人好道术,炼丹时以盐卤点成豆腐,因营养丰富且成本低廉,遂成平民菜。一方豆腐,成就了一座城,巍巍八公山上演绎了豆腐的千古传奇,两千年来,豆腐已从寿县传遍中国,远赴海外。
数月前,去淮南,二三人忽而兴起,结伴参观寿县豆腐文化馆,那一晚,大家在对面的八公山豆腐馆品尝了一桌“豆腐宴”,香酥豆腐、白玉豆腐饺、朱元璋豆腐、菊花豆腐……白瓷盘里,一道道美食,晶莹剔透、温润如玉,轻抿一口,唇齿之间,柔软、细腻,温和、恬静,滋味难以言说。
是夜,月色朗朗,风也和煦,那种快意,至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