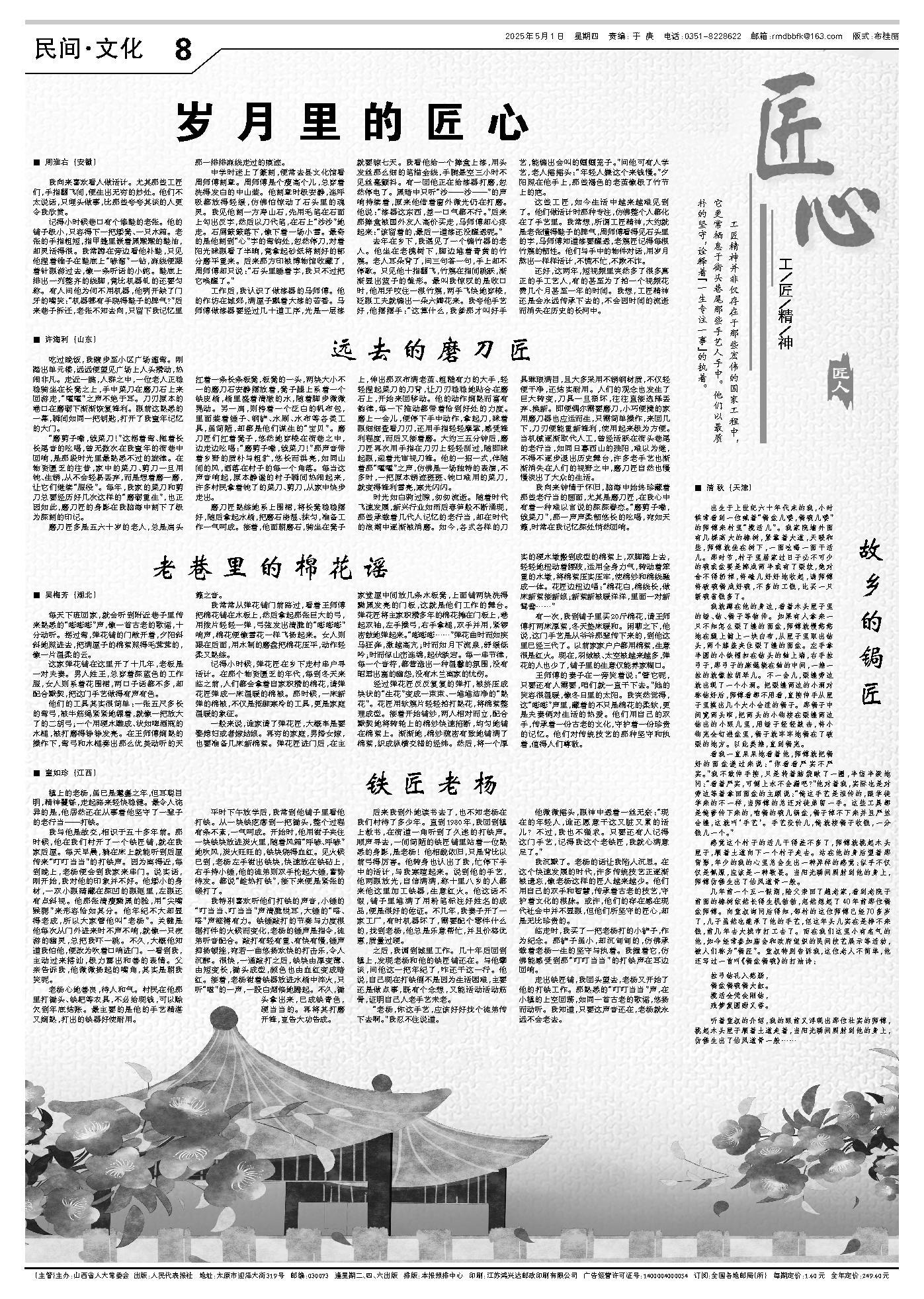■ 周淮右 (安徽)
我向来喜欢看人做活计。尤其那些工匠们,手指翻飞间,便生出无穷的妙处。他们不太说话,只埋头做事,比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更令我欣赏。
记得小时候巷口有个修鞋的老张。他的铺子极小,只容得下一把矮凳、一只木箱。老张的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黑黢黢的鞋油,却灵活得很。我常蹲在旁边看他补鞋,只见他捏着锥子在鞋底上“哧溜”一钻,麻线便跟着针眼游过去,像一条听话的小蛇。鞋底上排出一列整齐的线脚,竟比机器轧的还要匀称。有人问他为何不用机器,他咧开缺了门牙的嘴笑:“机器哪有手晓得鞋子的脾气?”后来巷子拆迁,老张不知去向,只留下我记忆里那一排排麻线走过的痕迹。
中学时迷上了篆刻,便常去县文化馆看周师傅刻章。周师傅是个瘦高个儿,总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他刻章时极安静,连呼吸都放得轻缓,仿佛怕惊动了石头里的魂灵。我见他刻一方寿山石,先用毛笔在石面上勾出反字,然后以刀代笔,在石上“沙沙”地走。石屑簌簌落下,像下着一场小雪。最奇的是他刻到“心”字的弯钩处,忽然停刀,对着阳光眯眼看了半晌,竟拿起砂纸将刻好的部分磨平重来。后来那方印被博物馆收藏了,周师傅却只说:“石头里睡着字,我只不过把它唤醒了。”
工作后,我认识了做漆器的马师傅。他的作坊在城郊,满屋子飘着大漆的苦香。马师傅做漆器要经过几十道工序,光是一层漆就要晾七天。我看他给一个捧盒上漆,用头发丝那么细的笔描金线,手腕悬空三小时不见丝毫颤抖。有一回他正在给漆器打磨,忽然停电了。黑暗中只听“沙——沙——”的声响持续着,原来他借着窗外微光仍在打磨。他说:“漆器这东西,差一口气都不行。”后来那捧盒被国外友人高价买走,马师傅却心疼起来:“该留着的,最后一道漆还没醒透呢。”
去年在乡下,我遇见了一个编竹器的老人。他坐在老槐树下,脚边堆着青黄的竹篾。老人耳朵背了,问三句答一句,手上却不停歇。只见他十指翻飞,竹篾在指间跳跃,渐渐显出篮子的雏形。最叫我惊叹的是收口时,他用牙咬住一根竹篾,两手飞快地穿梭,眨眼工夫就编出一朵六瓣花来。我夸他手艺好,他摆摆手:“这算什么,我爹那才叫好手艺,能编出会叫的蝈蝈笼子。”问他可有人学艺,老人摇摇头:“年轻人嫌这个来钱慢。”夕阳照在他手上,那些褐色的老茧像极了竹节上的疤。
这些工匠,如今生活中越来越难见到了。他们做活计时那种专注,仿佛整个人都化在了手艺里。我常想,所谓工匠精神,大约就是老张懂得鞋子的脾气,周师傅看得见石头里的字,马师傅知道漆要醒透,老篾匠记得每根竹篾的韧性。他们与手中的物件对话,用岁月熬出一样样活计,不慌不忙,不欺不诈。
还好,这两年,短视频里突然多了很多真正的手工艺人,有的甚至为了拍一个视频花费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我想,工匠精神还是会永远传承下去的,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