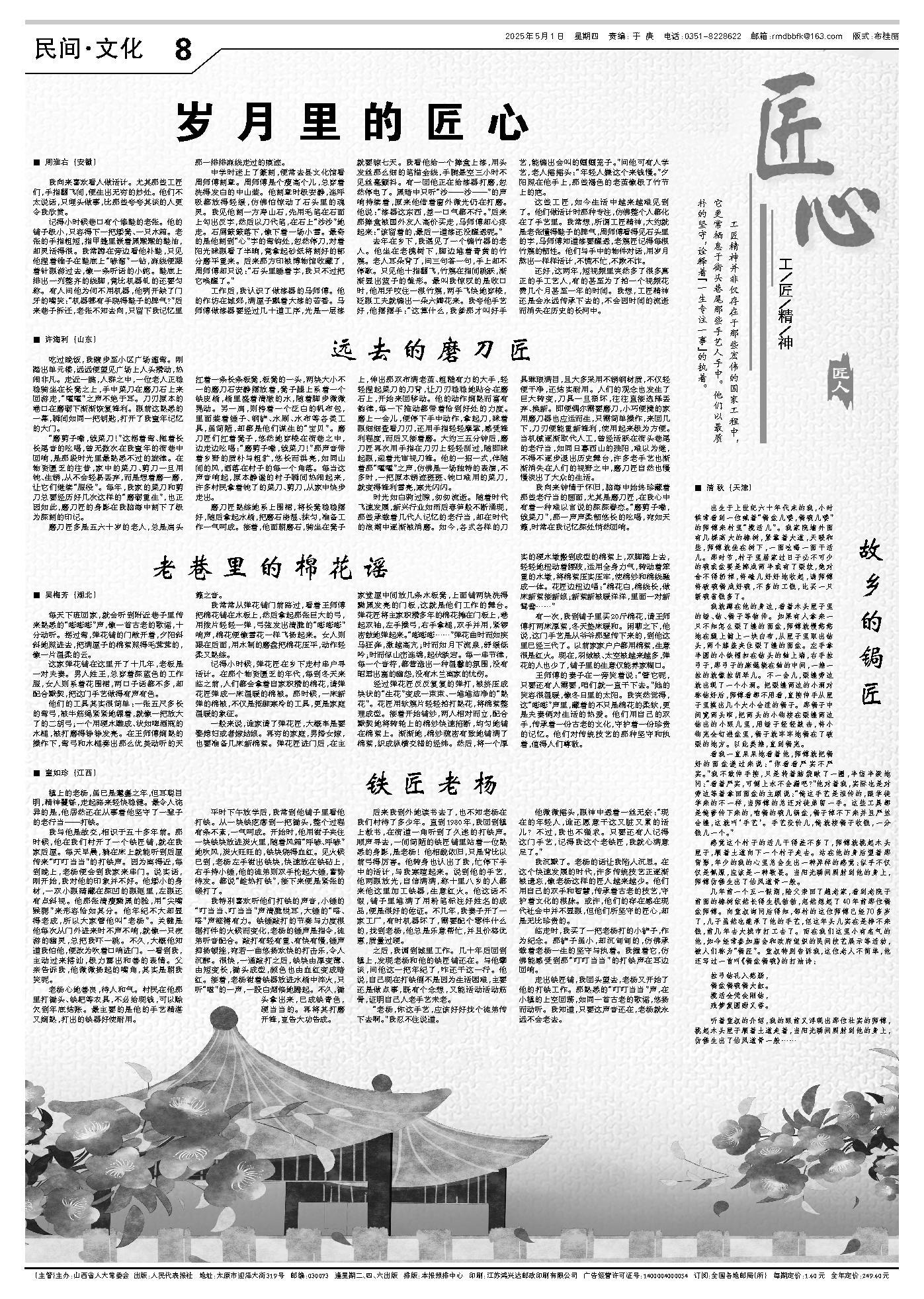■ 童如珍 (江西)
镇上的老杨,虽已是耄耋之年,但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走起路来轻快稳健。最令人诧异的是,他居然还在从事着他坚守了一辈子的老行当——打铁。
我与他是故交,相识于五十多年前。那时候,他在我们村开了一个铁匠铺,就在我家后屋。每天早晨,躺在床上就能听到后屋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因为离得近,每到晚上,老杨便会到我家来串门。说实话,刚开始,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矮小的身材,一双小眼睛藏在深凹的眼眶里,左眼还有点斜视。他那张清瘦黝黑的脸,用“尖嘴猴腮”来形容恰如其分。他年纪不大却显得老成,所以大家管他叫“老杨”。关键是他每次从门外进来时不声不响,就像一只夜游的幽灵,总把我吓一跳。不久,大概他知道我怕他,便改为吹着口哨进门。一看到我,主动过来搭讪,极力露出和善的表情。父亲告诉我,他微微扬起的嘴角,其实是朝我笑呢。
老杨心地善良,待人和气。村民在他那里打锄头、铁耙等农具,不必给现钱,可以赊欠到年底结账。最主要的是他的手艺精湛又娴熟,打出的铁器好使耐用。
平时下午放学后,我常到他铺子里看他打铁。从一块铁疙瘩到一把锄头,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一气呵成。开始时,他用钳子夹住一块铁块放进炭火里,随着风箱“呼哧、呼哧”地吹风,炭火旺旺的,铁块烧得血红。见火候已到,老杨左手钳出铁块,快速放在铁砧上,右手持小锤,他的徒弟则双手抡起大锤,蓄势待发。都说“趁热打铁”,接下来便是紧张的锻打了。
我特别喜欢听他们打铁的声音,小锤的“叮当当、叮当当”声清脆悦耳,大锤的“嗒、嗒”声铿锵有力。铁锤敲打的节奏与力度根据打件的火候而变化,老杨的锤声是指令,徒弟听音配合。敲打有轻有重、有快有慢,锤声抑扬顿挫,宛若一曲悠扬欢快的打击乐,令人沉醉。很快,一通敲打之后,铁块由厚变薄、由短变长,锄头成型,颜色也由血红变成暗红。接着,老杨钳着铁器放进水桶中淬火,只听“嗞”的一声,一股白烟倏地腾起。不久,锄头拿出来,已成铁青色,硬当当的。再将其打磨开锋,宣告大功告成。
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去了,也不知老杨在我们村待了多少年。直到1980年,我回到镇上教书,在街道一角听到了久违的打铁声。顺声寻去,一间简陋的铁匠铺里站着一位熟悉的身影,是老杨!他相貌依旧,只是背比以前弓得厉害。他转身也认出了我,忙停下手中的活计,与我寒暄起来。说到他的手艺,他两眼放光,自信满满,称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他这里加工铁器,生意红火。他这话不假,铺子里堆满了用粉笔标注好姓名的成品,便是很好的佐证。不几年,我妻子开了一家工厂,有时机器坏了,需要配个零件什么的,找到老杨,他总是乐意帮忙,并且价格优惠,质量过硬。
之后,我调到城里工作。几十年后回到镇上,发现老杨和他的铁匠铺还在。与他攀谈,问他这一把年纪了,咋还干这一行。他说,自己现在打铁倒不是因为生活困难,主要还是做点事,既有个念想,又能活动活动筋骨,证明自己人老手艺未老。
“老杨,你这手艺,应该好好找个徒弟传下去啊。”我忍不住说道。
他微微摇头,眼神中透着一丝无奈:“现在的年轻人,谁还愿意干这又脏又累的活儿?不过,我也不强求。只要还有人记得这门手艺,记得我这个老铁匠,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沉默了。老杨的话让我陷入沉思。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许多传统技艺正逐渐被遗忘,像老杨这样的匠人越来越少。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传承着古老的技艺,守护着文化的根脉。或许,他们的存在感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显眼,但他们所坚守的匠心,却是无比珍贵的。
临走时,我买了一把老杨打的小铲子,作为纪念。那铲子虽小,却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老杨一生的坚守与执着。我握着它,仿佛能感受到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在耳边回响。
走出铁匠铺,我回头望去,老杨又开始了他的打铁工作。那熟悉的“叮叮当当”声,在小镇的上空回荡,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悠扬而动听。我知道,只要这声音还在,老杨就永远不会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