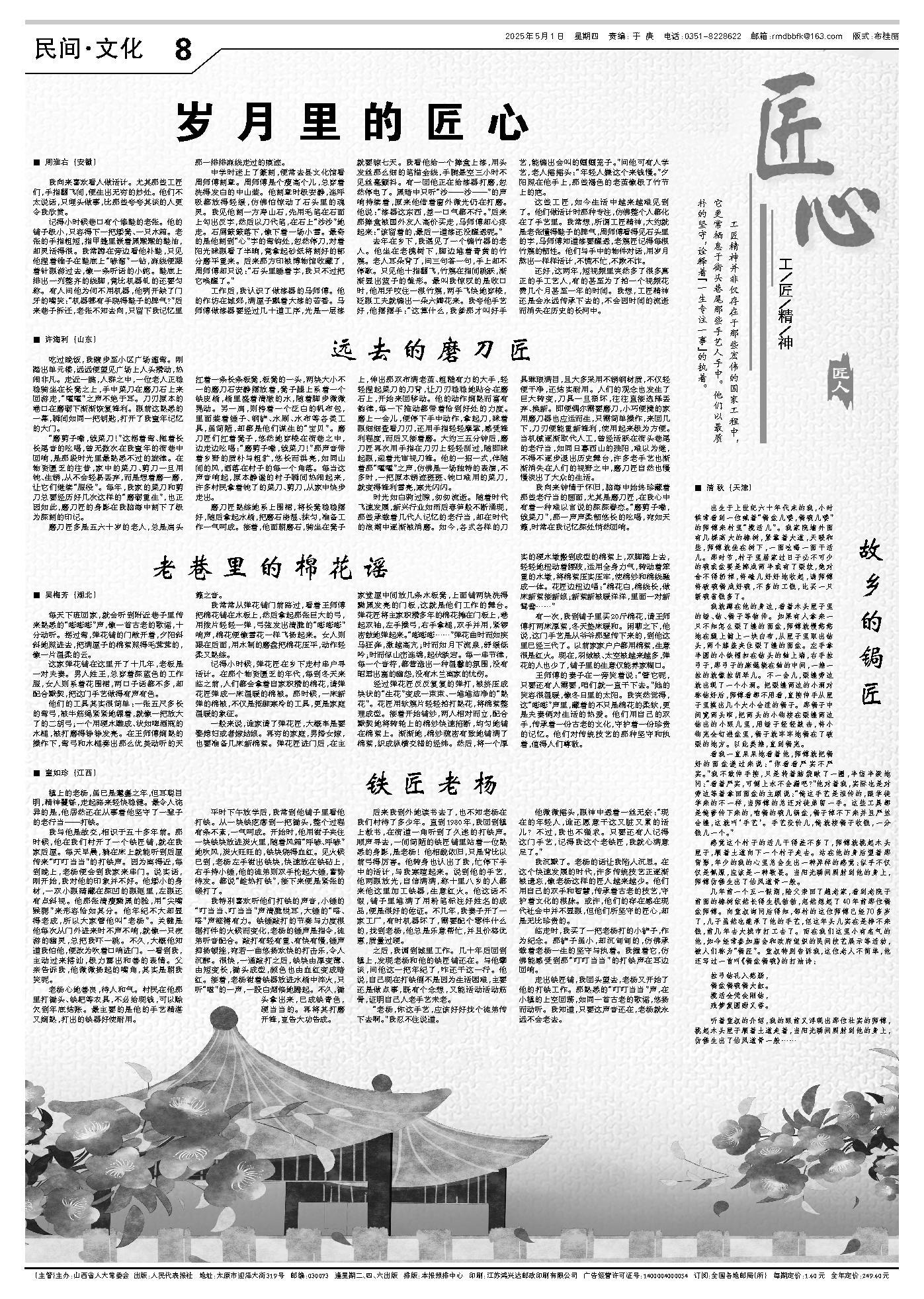■ 吴梅芳 (湖北)
每天下班回家,就会听到附近巷子里传来熟悉的“嘭嘭嘭”声,像一首古老的歌谣,十分动听。拐过弯,弹花铺的门敞开着,夕阳斜斜地照进去,把满屋子的棉絮照得毛茸茸的,像一片温柔的云。
这家弹花铺在这里开了十几年,老板是一对夫妻。男人姓王,总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女人则系着花围裙,两口子话都不多,却配合默契,把这门手艺做得有声有色。
他们的工具其实很简单:一张五尺多长的弯弓,被牛筋绳紧紧地绷着,就像一把放大了的二胡弓;一个用硬木雕成、状如啤酒瓶的木槌,被打磨得铮铮发亮。在王师傅娴熟的操作下,弯弓和木槌奏出那么优美动听的天籁之音。
我常常从弹花铺门前路过,看着王师傅把棉花铺在木板上,然后拿起那张巨大的弓,用拨片轻轻一弹,弓弦发出清脆的“嘭嘭嘭”响声,棉花便像雪花一样飞扬起来。女人则跟在后面,用木制的磨盘把棉花压平,动作轻柔又熟练。
记得小时候,弹花匠在乡下走村串户寻活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每到冬天来临之前,人们都会拿着自家积攒的棉花,请弹花匠弹成一床温暖的棉被。那时候,一床新弹的棉被,不仅是抵御寒冷的工具,更是家庭温暖的象征。
一般来说,谁家请了弹花匠,大概率是要娶媳妇或者嫁姑娘。再穷的家庭,男婚女嫁,也要准备几床新棉絮。弹花匠进门后,在主家堂屋中间放几条木板凳,上面铺两块洗得黝黑发亮的门板,这就是他们工作的舞台。弹花匠将主家积攒多年的棉花摊在门板上,卷起双袖,左手操弓,右手拿槌,双手并用,紧锣密鼓地弹起来。“嘭嘭嘭……”弹花曲时而如疾马狂奔,激越高亢;时而如月下流泉,舒缓低吟;时而似山峦连绵,起伏跌宕。每一串节律,每一个音符,都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没有昭君出塞的幽怨,没有木兰离家的忧伤。
经过弹花匠反反复复的弹打,被挤压成块状的“生花”变成一束束、一堆堆洁净的“熟花”。花匠用软篾片轻轻拍打熟花,将棉絮整理成型。接着开始铺纱,两人相对而立,配合默契地将转轮上的棉纱快速掐断,均匀地铺在棉絮上。渐渐地,棉纱疏密有致地铺满了棉絮,织成纵横交错的经纬。然后,将一个厚实的硬木墩搬到成型的棉絮上,双脚踏上去,轻轻地扭动着腰肢,运用全身力气,转动着笨重的木墩,将棉絮压实压牢,使棉纱和棉线融成一体。花匠边扭边唱:“棉花白,棉线长,做床新絮接新娘;新絮新被暖洋洋,里面一对新鸳鸯……”
有一次,我到铺子里买20斤棉花,请王师傅打两床厚絮,冬天垫床暖和。闲聊之下,他说,这门手艺是从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到他这里已经三代了。以前家家户户都用棉絮,生意很是红火。现在,羽绒被、太空被越来越多,弹花的人也少了,铺子里的生意仅能养家糊口。
王师傅的妻子在一旁笑着说:“管它呢,只要还有人需要,咱们就一直干下去。”她的笑容很温暖,像冬日里的太阳。我突然觉得,这“嘭嘭”声里,藏着的不只是棉花的柔软,更是夫妻俩对生活的热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传承着一份古老的文化,守护着一份珍贵的记忆。他们对传统技艺的那种坚守和执着,值得人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