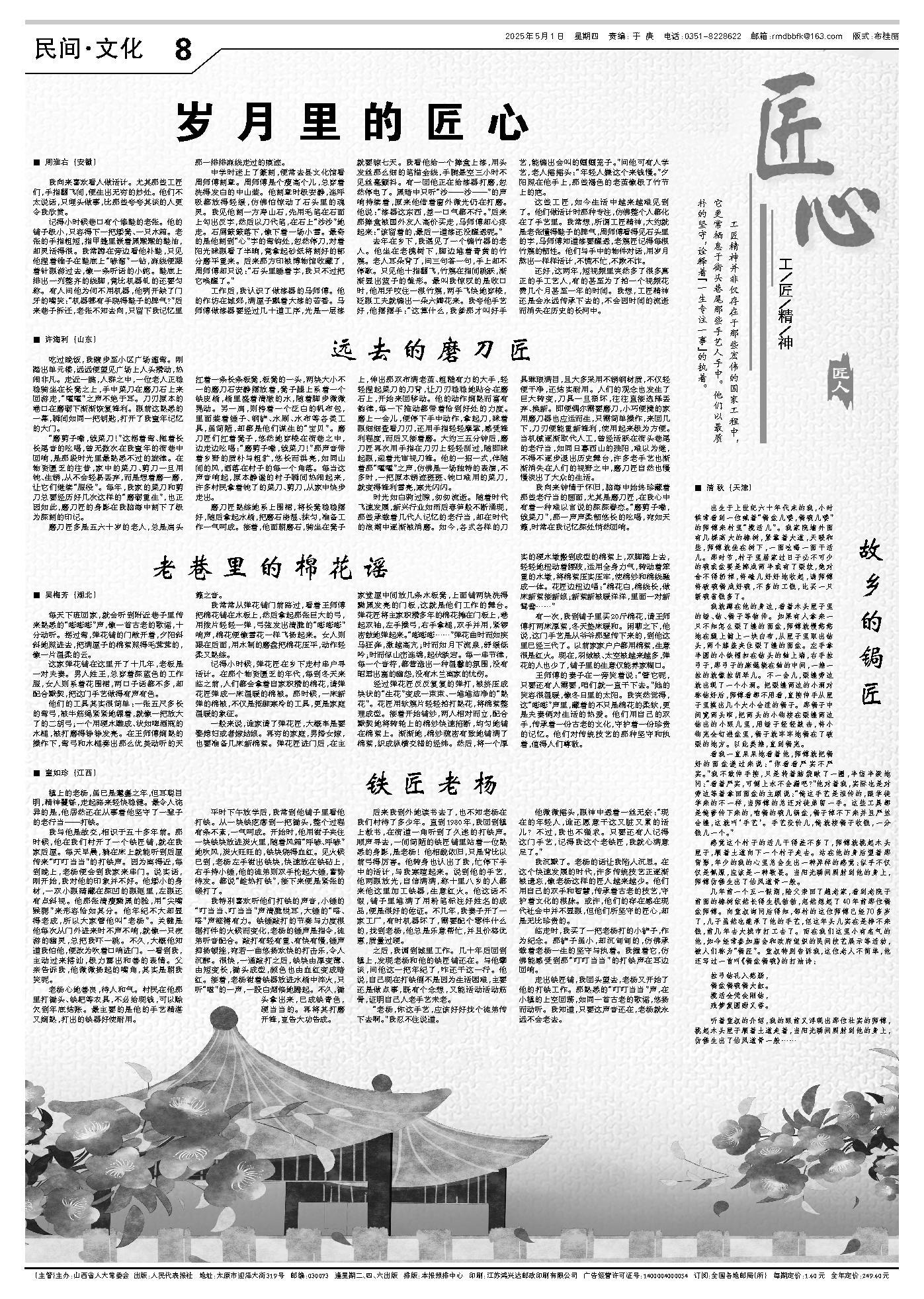■ 清 秋 (天津)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小时候常看到一位喊着“锔盆儿喽,锔碗儿喽”的师傅来村里“揽活儿”。我家院墙外面有几棵高大的椿树,紧靠着大道,天暖和些,师傅就坐在树下,一面吆喝一面干活儿。那时节,村子里居家过日子必不可少的碗或盆要是摔成两半或有了裂纹,绝对舍不得扔掉,将碴儿好好地收起,请师傅将破碗锔成好碗,不多的工钱,比买一只新碗省钱多了。
我就蹲在他的身边,看着木头匣子里的锤、钻、锔子等物件。如果有人拿来一只不知怎么裂了缝的面盆,师傅就慢悠悠地在腿上铺上一块白布,从匣子里取出钻头,两个膝盖夹住裂了缝的面盆。左手拿半圆的小铁帽扣在钻头的轴上端,右手拉弓子,那弓子的麻绳绕在轴的中间,一推一拉的就像拉胡琴儿。不一会儿,裂缝旁边就出现了一个小洞。把裂缝两边的小洞对称钻好后,师傅看都不用看,直接伸手从匣子里摸出几个大小合适的锔子。那锔子中间宽两头窄,把两头的小钩按在裂缝两边钻出的小眼儿里,用锤子轻轻敲击,将小钩完全钉进盆里,锔子就牢牢地锔在了破裂的地方。以此类推,直到锔完。
看我一直呆呆地看着他,师傅就把锔好的面盆递过来说:“你看看严实不严实。”我不敢伸手接,只是转着脑袋瞅了一圈,半信半疑地问:“看着严实,可倒上水不会漏吧?”他对着我,实际也是对旁边等着拿回面盆的主顾说:“俺这手艺是祖传的,跟学徒学来的不一样,当师傅的总还对徒弟留一手。这些工具都是俺爹传下来的,咱锔的碗儿锅盆,锔子掉不下来并且严丝合缝,这就叫‘手艺’。手艺没价儿,俺就按锔子收钱,一分钱儿一个。”
感觉这个村子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师傅就挑起木头匣子,顺着土道向下一个村子走去。站在他的身后望着那背影,年少的我的心里总会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不仅仅是佩服,应该是一种敬畏。当阳光瞬间照射到他的身上,师傅仿佛生出了仙风道骨一般。
几年前一个五一假期,陪父亲回了趟老家,看到老院子前面的椿树依然长得生机勃勃,忽然想起了40年前那位锔盆师傅。向堂叔询问后得知,邻村的这位师傅已经70多岁了,儿子虽然也继承了他的手艺,但这年头儿实在是挣不来钱,前几年去大城市打工去了。而在我们这里小有名气的他,如今经常参加庙会和政府组织的民间技艺展示等活动,被人们称为“锔匠”。堂叔特别告诉我,这位老人不简单,他还写过一首叫《锔盆锔碗》的打油诗:
拉弓钻孔入愁肠,
锔盆锔碗锔大缸。
揽活全凭金刚钻,
残梦复圆甜又香。
听着堂叔的介绍,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位壮实的师傅,挑起木头匣子顺着土道走着,当阳光瞬间照射到他的身上,仿佛生出了仙风道骨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