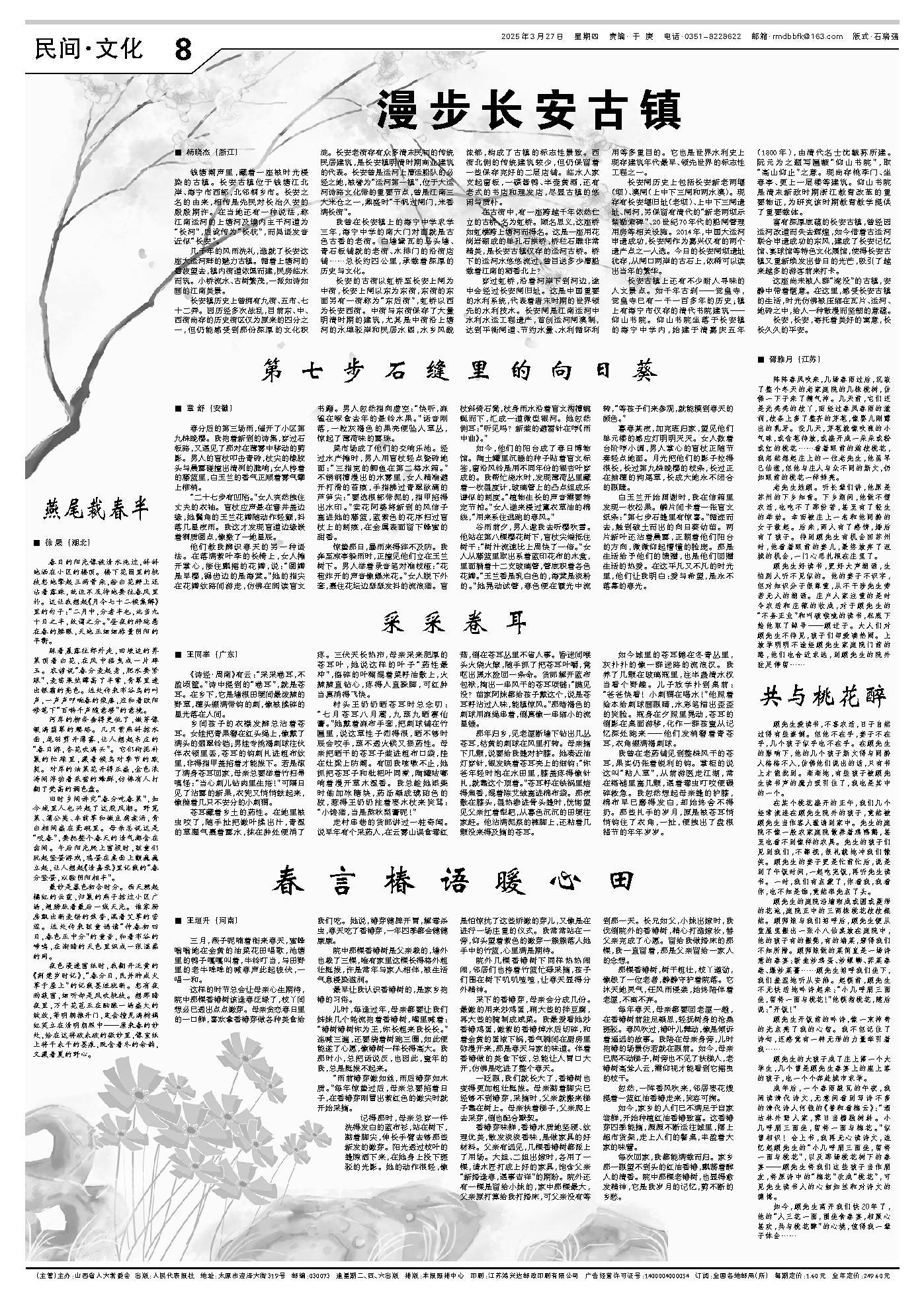■ 王同举 (广东)
《诗经·周南》有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诗中提到的“卷耳”,就是苍耳。在乡下,它是墙根田埂间最泼辣的野草,穗头缀满带钩的刺,像被揉碎的星光落在人间。
乡间孩子的衣襟发辫总沾着苍耳。女娃把青果簪在红头绳上,像戴了满头的翡翠铃铛;男娃专挑褐刺球往伙伴衣领里丢,苍耳的钩刺扎进粗布纹里,非得指甲盖掐着才能拔下。若是滚了满身苍耳回家,母亲总要举着竹扫帚嗔怪:“当心刺儿钻肉里生疮!”可隔日见了沾露的新果,衣兜又悄悄鼓起来,像揣着几只不安分的小刺猬。
苍耳藏着乡土的药性。在地里被虫咬了,随手扯把嫩叶揉出汁,青涩的草腥气裹着露水,抹在肿处便消了疼。三伏天长热疖,母亲采来肥厚的苍耳叶,她说这样的叶子“药性最冲”,捣碎的叶糊混着菜籽油敷上,火辣辣直钻心,疼得人直跺脚,可红肿当真消得飞快。
村头王奶奶晒苍耳时总念叨:“七月苍耳八月蒿,九蒸九晒赛仙膏。”她戴着麻布手套,把刺球铺在竹匾里,说这草性子烈得很,晒不够时辰会咬手,蒸不透火候又损药性。母亲把晒干的苍耳子装进粗布口袋,挂在灶梁上防潮。有回我咳嗽不止,她抓把苍耳子和枇杷叶同煮,陶罐咕嘟响着漫开草木涩香。我总趁她添柴时偷加冰糖块,药汤凝成琥珀色的胶,惹得王奶奶拄着枣木杖来笑骂:“小馋猫,当是熬秋梨膏呢!”
走村串巷的货郎讲过一桩奇闻。说早年有个采药人,在云雾山误食毒红菇,倒在苍耳丛里不省人事。昏迷间喉头火烧火燎,随手抓了把苍耳叶嚼,竟呕出黑水捡回一条命。货郎解开蓝布包袱,掏出一串风干的苍耳项链:“瞧见没?苗家阿妹都给孩子戴这个,说是苍耳籽沾过人味,能镇惊风。”那暗褐色的刺球用麻绳串着,倒真像一串缩小的流星锤。
那年归乡,见老屋断墙下钻出几丛苍耳,枯黄的刺球在风里打转。母亲摘下几颗,说要给我缝对护膝。她凑近油灯穿针,银发映着苍耳壳上的细钩:“你爸年轻时泡在水田里,膝盖疼得像针扎,就靠这个顶着。”苍耳籽在铁锅里焙得焦香,混着陈艾绒塞进棉布袋。那夜敷在膝头,温热渗进骨头缝时,恍惚望见父亲扛着犁耙,从暮色沉沉的田埂往家赶。他沾满泥浆的裤脚上,还粘着几颗没来得及摘的苍耳。
如今城里的苍耳蜷在冬青丛里,灰扑扑的像一群迷路的流浪汉。我养了几颗在玻璃瓶里,注半盏清水权当看个野趣。儿子放学扑到桌前:“爸爸快看!小刺猬在喝水!”他照着绘本给刺球画眼睛,水彩笔描出歪歪的笑脸。瓶身在夕照里晃动,苍耳的倒影在桌面游移,化作一群孩童从记忆深处跑来——他们发梢簪着青苍耳,衣角缀满褐刺球。
我曾在老药铺见到整株风干的苍耳,果实仍张着锐利的钩。掌柜的说这叫“粘人草”,从前游医走江湖,常在褡裢里塞几颗,遇着毒虫叮咬便碾碎救急。我忽然想起母亲缝的护膝,棉布早已磨得发白,却始终舍不得扔。那些扎手的岁月,原是被苍耳悄悄钩住了衣角,一扯,便拽出了盘根错节的年年岁岁。